
-
 专利
专利 -
 商标
商标 -
 版权
版权 -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
 反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 -
 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 -
 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
 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 -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律师动态
更多 >>知产速递
更多 >>审判动态
更多 >>案例聚焦
更多 >>法官视点
更多 >>裁判文书
更多 >>问题的提出
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以下简称“民诉解释”)颁布以来,在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管辖法院的确定问题上,出现了以下现象[1]:原告依民诉解释第25条选择其住所地法院起诉[2];被告则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20号,以下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第15条提起管辖权异议[3];法院通常简单地以 “两个法条并无冲突,可由当事人选择适用”为由驳回被告管辖权异议。[4]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程式化的判词虽然可以在个案中止息纷争,却因缺乏说理无法阻止更多的诉讼当事人将管辖权制度作为争夺自己预想利益的工具。
针对前述现象,笔者注意到有两篇文章展开了论述:一篇是孙远钊先生的《著作侵权诉讼管辖的冲突与解决》(以下简称“孙文”)[5],另一篇是邓宏光先生的《<民诉司法解释>互联网专条的适用(一)》(以下简称“邓文”)[6]。两篇文章均注意到了民诉解释第25条与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第15条的竞合问题,却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有效的讨论。而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管辖问题的核心恰恰在于选择这两个法条中的哪一个作为确定管辖法院的依据,同时将选定的法条进行明确化,以减少当事人管辖问题上的诉累。鉴于此,本文将以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管辖问题有关的法条(以下简称“管辖法条”)之间的冲突为切入点,回归管辖权制度的原点,对如何确定此类案件的管辖法院这一问题进行探讨[7]。
问管辖法条冲突的识别
适用法条之前,应先选择法条,尤其是多个法条在同一法律事实上相会时愈显重要。换句话说,“同一案件事实可以被多数法条指涉,大家称之为法条的竞合”。[8]法条竞合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构成要件相互包含或重叠且法律后果相互兼容,一种是构成要件相互包含或重叠但法律后果不相兼容。[9]后者又常被称之为法条冲突。然而,前述法条冲突理论貌似以实体法为模型建立,能否直接适用于程序法规定,不免令人生疑?其实不然。须知,不论实体性规定还是程序性规定,其均具备法律规范的一般特征,即拘束力。[10]因此,任何规定之间的冲突都必然表现在其赋予拟规制对象的法律后果之间的冲突上。
两个管辖法条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关键在于法律后果是否兼容,即两者对于作为管辖连接点之一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在法律后果评价上是否存在差异以致不能相容。[1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认为两者是并行关系,并无不一致的地方。[12]邓文亦持同样类似的见解。本文却持不同看法,主要理由如下:(1)从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第15条规定的字面含义看,该规定并没有将“侵权结果发生地”作为管辖连接点,其最后一句话亦仅仅是对“侵权行为地”的立法拟制。邓文认为:“该规定采用的词语是‘包括’,而非‘限于’, ‘包括’仅仅是列举了典型情形,但其范围显然不应当仅仅限于典型情形,因此,不能因为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的这条规定,而将侵权行为结果地作为管辖地予以排除。” 这一观点未免过于简单草率。因为该规定中“包括”一词乃与后面的“等”字对应,列举的对象是实施侵权行为的设备,所以能够扩大适用范围的也只能是设备本身而非侵权行为,显然不能由此推论出可以包括“侵权结果发生地”(2)退一步讲,即使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第15条规定的最后一句话解读为包括“侵权结果发生地”,其与民诉解释第25条的规定也不兼容。首先,在确定“侵权结果发生地”内容方面存在差异:前者为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后者为被侵权人住所地。其次,在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条件方面存在差异:前者的适用以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为前置条件,后者无任何适用限制条件。一言以蔽之,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第15条规定只能有 “不包括侵权结果发生地”或者 “有条件地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两种解释情形,而不论采取哪一种解释,都与民诉解释第25条规定在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作为管辖连接点方面存在冲突。
管辖法院的确定
既然管辖法条之间存在冲突,接下来便需讨论依何种冲突类型对应的选择机制去选择合适的法条,进而据此确定相应的管辖法院。
(一) 冲突类型的确定
法条冲突的类型大致分为三种情形:时间冲突、空间(权力等级)冲突和逻辑冲突。[13]民诉解释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均为同一机关颁布,故不可能存在空间冲突。根据两个司法解释的生效时间来看,民诉解释属于新法,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属于旧法,当属无疑。因此,两个解释中管辖法条的逻辑关系自然是探讨重点之所在。
法条之间所谓逻辑上的特殊关系意指:“特殊规范的适用范围完全包含于一般规范的适用范围内。”[14]从字面来看,民诉解释25条中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主要有两层含义:(1)在信息网络中实施侵权行为,即信息网络是实施侵权行为的场所和环境;(2)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侵权行为,即信息网络是实施侵权行为的手段。由于侵权是对行为本身定性,行为场景并不影响定性,故后一种解释更为可取。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指出:“民诉解释第25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具有特定含义,指的是侵权人利用互联网发布直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的行为,主要是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以及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行为,即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等均在信息网络上,并非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与网络有关即可认定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15]显然,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第15条只适用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而民诉解释第25条可以适用于包括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在内的其他利用信息网络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综上所述,民诉解释第25条属于新的一般规定,而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第15条属于旧的特别规定。
(二)冲突类型之间的矛盾消除
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冲突解决规则,应该适用民诉解释第25条;相反,根据“特殊规定优于一般规定”,应该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第15条。此时,时间冲突和逻辑冲突交叉出现在同一法条之上,产生了需要消除的选择矛盾。然仔细探究,不难发现,无论是“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抑或是“特殊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冲突解决规则,归根结底,实际上均是立法者意志使然。这也进一步佐证了立法法为何在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情况下需要制定机关进行裁决。[16]所以,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冲突时,依然要按照立法者的取舍为判断依归。对此,德国学者平特纳即认为:“较新的一般法律只在适当的解释中表明废除旧的特别法律时方优于旧法(否则旧法仍作为特别法或例外规定继续有效)……任何新法律的立法者未明确表示要废除或优先于现行法律时,即意味着立法者欲把新法作为现行法的补充。”[17]国内学者基本也持前述观点。[18]
基于民诉解释第552条的规定,并结合民诉解释起草人对该解释第25条的解读可以看出,立法者已经明确放弃原本规定在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第15条的“原告发现侵权信息内容地”作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的法院管辖地。[19]因此,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的管辖法院应该按照民诉解释第25条进行确定。需补充说明的是,对于管辖权规定这样一种不涉及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程序性规定,应该以诉讼发生时(而非行为发生时)作为选择法律规定的时间判断基准点。
(三)对“侵权结果发生地”的限缩解释
选择恰当的法条并不代表法条的恰当适用。尽管选择民诉解释第25条作为确定管辖法院的依据已经得到明确,但是仍需厘清该规定中“侵权结果发生地”作为管辖连接点在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适用上的内涵,方能减轻此问题上无谓争论所导致的诉讼负担。这一点并非如现有著作所述的那样:“诉讼程序上的许多制度往往通过日积月累的司法实务以‘相沿成袭’或‘约定俗成’的方式逐渐形成,并不一定能够也未必总是需要理论说明。管辖制度上有不少地方或内容属于此种情形。”[20]“界定(管辖连接点的选择—笔者注)可以约定俗成,判断(管辖连接点的解释—笔者注)却并非约定俗成。”[21]前述观点充其量说明立法者在符合管辖连接点确定标准的诸多连接点中选取哪一个进行规定多少有点约定的成分,这并不代表管辖连接点的确定本身无标准,更不代表管辖连接点确定后可以任意解释。
“与当事人有关的任何因素如果能够成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因素自身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稳定性,至少是可以确定的;二是该因素自身与管辖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度。”[22]对于民诉解释第25条规定将“侵权结果发生地”解释为“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根据前述标准便可以看出,“被侵权人住所地”仅具有确定性,却无法通过侵权结果这一因素与法院产生关联。无怪乎最高人民法院反复重申:“侵权结果发生地应该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的发生地,不能以权利人认为受到损害就认为其住所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23]由前文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定义可知,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中侵权行为的直接结果应该发生在网络上,故被侵权人在网络上发现的侵权信息内容才是侵权结果。因此,立足于侵权结果这一概念的内涵,遵从管辖连接点确定标准,在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中应该对民诉解释第25条中的“侵权结果发生地”作限缩解释:侵权结果发现地包括能够发现侵权信息内容的被侵权人住所地。这一解释既保证了管辖地的关联性(能够发现侵权信息内容),又保证了管辖地的确定性(被侵权人住所地),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统一。
也许前述限缩解释会遭到如下质疑:两者在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的管辖适用上有何区别?最后落脚点仍然会回到“被侵权人住所地”,难免有叠床架屋之嫌。此时,不妨回顾一下民诉解释确定“侵权结果发生地”作为管辖地的立法初衷。民诉解释的起草者说明“侵权结果发生地”作为管辖地的立法背景时,曾提出:“在本次司法解释的制定过程中,考虑到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很多涉外案件,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实施地均在国外,而侵权结果发生在国内,如果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无法行使管辖权,则不能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24]可见,“侵权结果发生地”作为管辖地,乃是针对涉外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而设。在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涉外案件中,确定管辖法院需要重点考虑的是涉外网站活动是否针对本国公众或者对本国公众造成影响。[5]否则,仅凭“被侵权人住所地”在本国就确定管辖法院,不仅可能会造成国家之间管辖权冲突,甚至会导致本国判决在其他国家得不到承认和执行。为此,“侵权结果发生地”的限缩解释对国内案件适用确实无甚差别—国内不太可能分地域上网,却对涉外案件适用至关重要。[26]唯适用时需要注意的是,因民事诉讼法第259条间接排斥了民诉解释第24条和第25条的直接适用,故只能将本文对民诉解释第25条中“侵权结果发生地”的限缩解释结论类推适用至民事诉讼法第265条。[27]
余论
管辖权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分配制度,是先验抽象地假定各级法院审判公正的情况下,将不断发生的案件分配予已经给定的、处于一定区域的法院。申言之,管辖权是法院内部的合理分工制度,分工主要依据在于方便法院审理和执行案件,与实体正义并无多大关系。[28]基于管辖权制度这一目的,只要当事人提交的符合法院受理条件的证据材料能证明存在相应的管辖连接点以便可以确定管辖法院,管辖权制度的使命即告完成。鉴于此,尽管前文通过结合“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概念以及管辖连接点确定标准对民诉解释第25条中的“侵权结果发生地”进行了限缩解释,但这仅仅是为了从概念上厘清管辖连接点的内涵以保证适用的明确性,而绝不意味着要求确定管辖法院的过程中需要预先判断被控侵权人相应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29],不可不察。
注释:
1. 这只是约略陈述,而非全称陈述,不可混淆,两者区分可参见:李天命:《杀闷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2. 民诉解释第25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
3. 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第15条规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所在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视为侵权行为地。
4. 相关裁定可参见:(2015)京知民终字第1047号;(2017)粤民辖终646号。
5. 参见孙远钊:《著作侵权诉讼管辖的冲突与解决》,载“知产库”微信公众号,2018年9月12日。
6.参见邓宏光:《<民诉司法解释>互联网专条的适用(一)》,载“中国知识产权杂志”微信公众号,2018年9月30日。
7. 管辖分为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级别管辖随地域管辖而确定,故本文主要讨论地域管辖这一更为基础问题,特此说明。
8.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6页。
9. 将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区分为包含和重叠,主要见于德国学者的观点,具体可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7页;[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此外,尚有国内学者和台湾学者认为构成要件之间有重合关系,具体可参见:舒国莹、王夏昊、雷磊:《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页;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不过本文认为,重合可以分为部分重合和完全重合,部分重合可以归入重叠(实际上黄茂荣先生也只是在部分重合意义上论述构成要件关系,其所述的构成要件重合和交集与德国学者所述的构成要件重叠并无本质区别)。至于完全重合,不论法律后果是否兼容,均属难以想象的立法,尤其是在法律后果不兼容的情况下,会因难以适用任何冲突解决规则形成“碰撞漏洞”,导致两个法律规范都无法适用的局面,故本文不采纳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可以包括重合的观点。
10. 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11. 对于侵权行为实施地这样一个管辖连接点,两个规定之间并无区别,故无讨论的必要。
12. 参见注释4。
13. 尽管文中冲突类型的划分在立法法中是针对法律规定而言,但由于立法法第104条委婉承认了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故该冲突类型的划分同样可适用于司法解释的规定。
14. 同注释8。
15. (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3号。
16. 根据对立法法第94条规定的反面解释,在能够确定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如何适用时,自然无需制定机关进行裁决。
17. 转引自杨登峰:《法律冲突与适用规则》,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8页。
18. 参见陈运生:《法律冲突解决的进路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页;刘志刚:《法律规范的冲突解决规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沈志先主编:《法律方法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页;舒国莹、王夏昊、雷磊:《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6页;孔祥俊:《法律解释与适用方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594页;胡建淼:《法律适用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3页;也有学者认为应无条件适用旧的特别规定优于新的一般规定(台湾地区“中央法规标准法”第16条亦如此规定,不过,“台湾最高法院”在适用中作了灵活变通,有兴趣者可参看前引学者著述,不再赘述), 但该观念与立法法94条规定的精神不符,为本文所不取,具体可参见陈金钊等:《法律方法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该部分为董淑萍撰写;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应无条件适用“新的一般规定优先于旧的特别规定”,但并未提供任何理由,也不符合学界共识,具体可参见:郑永流:《法律方法论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19. 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页。
20. 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
21. 同注释1,第151页。
22. 徐冬根:《国际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4页。
23. 同注释15,另可参见:(2013)民提字第16号。
24. 同注释19,第173页。
25. 参见冯术杰:《通过国际网络进行的商标侵权行为的管辖与认定—法国的相关判例及其启示》,载氏著《知识产权法:国际的视野与本土的适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9-363页。
26. 正如孙文所述,如果包括原告在内的任何在中国境内的自然人或法人,以现行合法的方式上网根本无法接触到被告完全位于境外的产品,此时法院依然行使管辖权会导致“管辖过剩”。
27. 邓文认为民事诉讼法第265条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没有适用空间,显然是没有注意到该规定中存在“侵权行为地”作为管辖连接点。
28. 参见张卫平:《管辖权异议:制度原点与制度修正》,载氏著《民事诉讼:回归原点的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2-366页。原文标题为《管辖权异议:回归原点与制度修正》,载于《法学研究》2006第4期。
29. 广东高院持同样见解,可参见注释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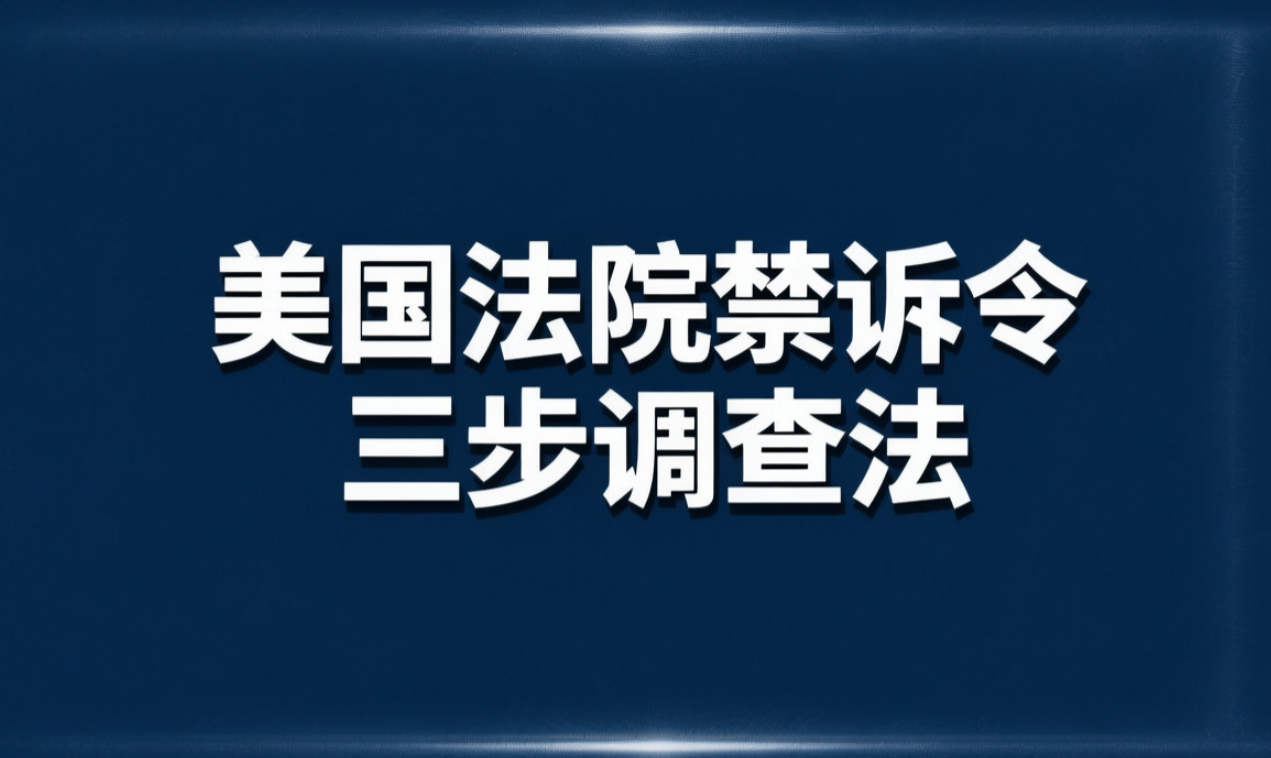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上一篇
上一篇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