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专利
专利 -
 商标
商标 -
 版权
版权 -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
 反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 -
 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 -
 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
 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 -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律师动态
更多 >>知产速递
更多 >>审判动态
更多 >>案例聚焦
更多 >>法官视点
更多 >>裁判文书
更多 >>原标题:特别策划 | 漫谈“智能剪辑”短视频版权二三事
“仅需一张照片,出演天下好戏”,近日,一款名为“ZAO”的手机软件一夜之间火遍各大社交平台。通过该款手机软件,普通用户可以将某些影视剧片段中的人物面部替换为自己的肖像,并可以保存和发布“换脸”后的视频。“ZAO”软件“造”的主要是短视频。在实践中,短视频可以有多种分类,例如从内容生产方式上,可以将短视频分为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指平台普通用户自主创作并上传的短视频内容,普通用户非专业的个人生产者)、PGC(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指专业机构创作并上传的短视频内容)和PUGC(Professionally User Generated Content,指平台专业用户创作并上传的短视频内容)[1]。“ZAO”的短视频大体可以归为UGC,由于在社交平台上普通用户毕竟是多数,其并不以制作视频为业,专业程度也不高,本文的讨论将集中在UGC上。
在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和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ZAO”也较为典型的代表了一类通过“智能剪辑”制作短视频的新模式。与传统的视频剪辑不同,在“智能剪辑”平台上,用户可以通过简单地进行设置主题、上传素材或利用平台提供的素材,由软件或者平台自动生成剪辑后的短视频,甚至实现“一键剪辑”。
“智能剪辑”短视频因其受众年轻化、模式多样化、社交互动性强,且便于传播,具备成为“爆款”和“网红”条件。“ZAO”软件即一度出现了软件服务器“不堪重负”的情况。然而,该手机应用在风靡社交平台时,也在各界引发了热烈讨论,例如用户协议中的用户给“ZAO”的授权范围和承诺内容、著作权及肖像权侵权问题等,“ZAO”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内容也是一改再改。目前,“ZAO”的热度似乎有所降温,但“智能剪辑”短视频相关版权问题恐怕还要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讨论。笔者拟以此拙作抛砖引玉,与广大读者探讨。
1. 效率削减独创性
不论哪种剪辑模式,由于这类短视频源于已有作品或素材,因此其要么是对原作品或素材的复制,要么就是出现了新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虽然学理上对独创性标准的理解莫衷一是,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独创性标准的门槛不高。独创性的两个要素可以归纳为独立完成并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2]。对于“智能剪辑”短视频而言,其是否为独立完成?由谁独立完成?是否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都有值得探讨的空间。司法实践中,对于“独”的把握比较统一,而对于“创”的认定,司法实践中的裁量空间较大,有“是否为个性化的表达”、“是否为自主意识下的选择、取舍、加工的结果”、“是否会对公有领域产生影响”、“是否有新颖性”等标准[3]。
对于传统意义上剪辑产生的短视频而言,其中大部分都通过整合、筛选,再加上新的配乐、图片并进行拼接糅合,传达出了和原作品完全不同的思想。如将超级英雄系列的电影中超级英雄们受伤后坚持为正义而战的短画面拼接在一起,配上有节奏感的音乐,不仅将主体进一步升华、浓缩,也给观看者带来更多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受。笔者认为这类产生具有独创性的完整表达的短视频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并无争议。
而“智能剪辑”短视频则更可以被理解为人利用计算机软件、程序所生成的成果,该等成果是否包含新的独创性的表达,进而可能能够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可能需要个案分析。为了吸引用户,根据笔者的经验,有些软件的娱乐性、消遣性较重,通过对现有作品或素材中的某一元素进行调整、置换,或是将片段进行重复、倒放、变速,以达到抖包袱、引人发笑的效果。相应地,该类“智能剪辑”在操作门槛上较低,用户只需要简单的点击、设置即可产出相应视频。智能化的“一键操作”虽然带来了效率,但这种效率可能会牺牲对素材的选择、提炼、加工,甚至完全看不到用户“个性化的火花”。如果是纯粹的“人工智能”输出或者人的参与可以忽略不计,其作品属性亦将被质疑[4]。当然,也有部分“智能剪辑”软件虽然最后也是一键生成短视频,但其智能化程度较高,例如可基于一篇文案逆向“配出”视频,或者为用户提供了更多前置选择步骤等等,该等“智能剪辑”短视频显然更容易满足“独创性”的要求。
2. 权利归属的选择
“智能剪辑”短视频的权利归属于谁,可能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智能剪辑”短视频本身无法构成作品时不必讨论著作权归属问题。但是,“智能剪辑”短视频承载的商业价值越来越大,对其权利归属不能置若罔闻,“智能剪辑”短视频中“创”的来源亦日趋复杂,对其作品属性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对其权利归属作出选择仍是有意义的。
如果用户进行了选择、编排并融入了自己的思想、个性,其成为作者通常将没有争议。但有争议的是,在实践中,用户往往只需要简单上传几个文件、设置某一些简单的关键词和条件,即可“一键生成”短视频。尽管“智能剪辑”的智能化程度可能很高,例如能够根据用户输入的文案自动匹配和生成相应的短视频,但这个过程是用户在“独创”吗?笔者持怀疑态度。可能有人会认为,是软件的制作者将诸多智能化的功能整合到一起,程序、软件运行时进行的选择、编排、提炼、加工实际上就是代表的软件制作者的思想,其付出了创造性劳动,参考计算机游戏画面著作权归属问题上的主流观点,此时应当成为作者。但是,“智能剪辑”短视频不是简单的程式化内容生成的结果,软件制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仅存在于软件制作的过程中,其产出的软件作品已经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如果让其对软件作品继续享有当然控制的权利不尽合理,故笔者也不敢苟同这种论断。
在两个可能享有著作权的主体都有些“牵强”时,或许有人会主张智能软件、程序本身作为“人工智能”,能够作者为著作权法的主体。这个话题在近年来也被热议。但根据目前的主流观点,不论从人工智能生成成果是否构成作品的角度,还是从权利归属的角度,“人工智能”都很难成为作者。尤其是,目前的社交平台上的这一类程序软件还远没有达到人工智能的程度,也就更无所谓其被认定为作者的问题。
在“菲林诉百度一案”中,一审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也认为民法主体的规范不应当被突破[5]。值得注意的是,在“菲林诉百度一案”案中,北京互联网法院在认为“即使威科先行库‘创作’的分析报告具有独创性,该分析报告仍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依然不能认定威科先行库是作者并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相关权利”之后,在权利保护层面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似乎是“威科先行库‘创作’的分析报告”可通过“相关权益”进行保护并实现价值,且该等“相关权益”应归属于软件的使用者(即用户)。
笔者认为,上述做法可能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创作”的主体无法突破“自然人”时的“权宜之计”,且有相当的合理性,除该案判决中提到的“传播动力”考量外,至少从归属上看,“智能剪辑”平台作为商事主体,在实力、资本、谈判地位上都比普通用户有更大的优势。如果把“相关权益”分配给他们,无疑再次巩固了这种优势,用户将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上述做法尽管表面上解决了“智能剪辑”短视频的保护和归属问题,“相关权益”显然无法像著作权那样名正言顺的包括各具体权项,进而有利于促进文化创作和传播。
笔者认为,从参与程度上看,普通用户的“创作”行为在实践中存在模糊地带,但即便“创”的色彩有限,但在软件使用环节,相比“智能剪辑”平台(其基于开发的“智能剪辑”软件已经享有版权,其提供的可用于剪辑的“内容库”至少可被一类用户共用),普通用户对“智能剪辑”短视频的形成参与程度更高,至少有上传照片、选择剪辑对象等行为,有些情况下普通用户的“创”的色彩更大。从结果表现上看,智能程序、软件的确朝着摆脱事前设计,参与或直接创作的方向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计算机已接近能够在脱离人工参与的情况下实现独立生成内容,如果抛开主体因素,相关内容完全满足“独创性”要求,与人工剪辑的成果无异。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提供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为了提供创作动机,以扩大相应成果的供给[6];同时能够赋予交易双方合理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易达成[7],如果有著作权权项的“加持”,对“智能剪辑”短视频的后续使用、传播显然也将更为有序和高效。
因此,在实践中“智能剪辑”平台不妨不要过度纠缠于对“智能剪辑”短视频在法律上的“应然定性”,而是根据商业需求与普通用户签署合理、有效的用户协议,并将“智能剪辑”短视频视为作品,将作者视为普通用户。进而,“智能剪辑”平台可根据自身商业需求,就“智能剪辑”短视频的后续使用,例如复制、信息网络传播等,与普通用户达成合意,获得授权许可。如果涉及个人隐私和肖像权的上传,“智能剪辑”平台还应当制定合理的隐私政策和声明。当然,由于用户自己也可能会上传内容,“智能剪辑”平台在用户协议中通常会要求用户承诺就上传的内容享有合法权利或获得合法授权。如此,不仅能够更有利地保障用户提供内容上承载的包括肖像权在内的权利/权益,而且有利于平台为使用来源于用户的内容预留合法的空间、圈定较为清晰的使用边界,此时,平台为使用之目的也势必会提供更细致、公平的许可协议,实际成为了对平台的一种督促。同时,该等做法也解决了类似“会给普通用户过度赋权”的问题,因为普通用户作出的短视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用户的烙印(例如“换脸”),但其如果想使用,仍难以摆脱原始作品的羁绊。
3. 合理使用难以适用
如果完全使用不受版权保护的元素或素材进行独创性的剪辑、混剪,则产生的包含独创性表达的成果不受在先著作权的“羁绊”。目前,“智能剪辑”平台的商业模式通常涉及对原始作品的复制、演绎、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已有部分平台供用户“剪辑”的内容是直接收集或经拆分处理后的片段或元素,但是否仍有他人就该等片段或元素享有版权仍受到该等片段或元素的具体情况、授权链条等的影响。故此处仍值得讨论的是对原始作品或其中构成作品的内容进行“智能剪辑”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问题。
与美国通过“四要素”法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不同,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合理使用条款为封闭条款,不存在一般性适用的条款。当然,我国司法实践也有借鉴四要素的操作。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中有提到对被使用部分的数量、使用比例、对作品正常使用的影响等因素的考虑。但是,相关考虑并没有直接突破合理使用的封闭性。
与此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美国版权法上的“转换性使用”。“转换性使用”这一术语最早是在1990年由皮埃尔·莱托(Pierre Leval)提出[8]。其认为,若要构成合理使用,二次作品必须要在原作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具有其他目的或不同的性质,创作出新的信息、新的美学、新的认识和理解。这种情况下对他人作品的使用才会有益于社会,才是合理使用制度应该保护的行为。在1994年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一案中,“转换性使用”的观点首次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对原作戏仿并未取代原作,而是增加了新的内容,以新的表达、含义或意义改变了原作,属于转换性使用,因而认定此种行为构成合理使用[9]。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以“转换性使用”为关键词在知产宝数据库中进行检索,虽数量不多,但也可以见到“转换性使用”的身影,且在认定思路上和美国版权法上的“转换性使用”基本一致,即要求不能实质性地取代原作(再现原作的表意功能)进而对作者正常使用原作造成影响,且可以实现新的意义或功能[10]。
在本文语境下,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合理使用条款中,适用可能性最大的只有可能是第(二)项,即“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但纵观现有的智能剪辑程序、软件,例如“ZAO”平台,其目的更接近娱乐,特点在于对已有作品中某一个元素的替换,而非介绍、评论该作品或说明某一问题。再例如鬼畜视频生成软件,仅是将片段进行重复、倒放、拼接。笔者认为行为的机械性、简单性和娱乐性,使得将类似“智能剪辑”平台的用户行为沿着“介绍、评论、说明”路径进行解释存在困难,很难纳入合理使用的范围。同时,也很难符合“转换性使用”的要求。
可见,在用户作出的短视频很难从原始作品相关复制权与演绎权的控制中逃逸的情况下,“智能剪辑”平台商业模式的开展需要获得原始作品权利人的授权,且该等授权通常应由“智能剪辑”平台寻求获取,因为用户显然不可能对万千用于剪辑的内容一一寻找对应的权利人。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能买断原始作品或其中构成作品的内容,“智能剪辑”平台获得完整的、充分的授权至关重要,但并非易事。对此, “智能剪辑”平台一定要结合自身业务模式和“智能剪辑”流程,确保每一环节的行为都获得必要的授权,尤其应当特别注意在剪辑的方式、动机五花八门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在涉及原始作品中明星肖像时如何避免侵犯人身权等问题。当然,提及授权许可,就必然存在获得何种授权、向谁获得授权、获得多大范围授权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不再展开。
综上,在UGC的情景下,“智能剪辑”的“智能性”为普通用户省去了“创”的付出步骤,“娱乐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普通用户个性的融入,导致“智能剪辑”短视频包含的普通用户独创性表达不会太多或者存在“模糊地带”。但在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出现之前,人的参与仍然不可或缺,在智能化程度越高的情况下,抛开创作主体问题,“智能剪辑”短视频的“独创性”已经越来越倾向于能够与传统的人工剪辑媲美。笔者认为从实然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权利保护、交易便利、可能的权利滥用等因素,“智能剪辑”平台在商业活动中不应也不必回避模糊地带,即便在用户参与极少的情况下,亦可将“智能剪辑”短视频视为作品,并将普通用户视为作者,通过用户协议以“合意”的方式约定生成的“智能剪辑”短视频及内容的归属和后续使用,获得“来源于用户的授权”。在合理使用通常不能适用的情况下,“智能剪辑”平台应充分重视就提供给用户,供用户剪辑内容获得完整、充分的授权,以便结合自身商业模式,获得“来源于权利人的授权”。做好上述两方面授权后,“智能剪辑”平台与用户将进入“良性互动”,平台得到了其需要的流量、知名度和不断丰富的“内容库”,用户在体验娱乐的同时不必担心侵犯在先权利人知识产权,自身权利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最后,作者相信,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剪辑”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层出不穷并吸引人们的眼球,但随着人们对技术认识的不断发展甚至对“表达的前提乃自然人所独有的智力或思想” [11]观念可能的突破,“智能剪辑”短视频的可版权性、权利归属问题等还将会不断被讨论。
注:实习生黄啸枫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 孙飞,张静.短视频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J].电子知识产权,2018(05):65-73.
[2] 崔国斌. 著作权法:原理与案例[M]. 2014.
[3] 张雯,朱阁.侵害短视频著作权案件的审理思路和主要问题——以“抖音短视频”诉“伙拍小视频”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为例[J].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9(06):3-14.
[4] 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05):148-155.
[5](2018)京0491民初239号民事判决书
[6] 崔国斌.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J].中国法学,2006(01):144-164.
[7] Demsetz, H. . (1974).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2), 347-359.
[8] Leval, P. N. (1990). Toward fair use standard. Harvard Law Review 103(5), 1105-1136.
[9]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 510 U.S. 569, 114 S. Ct. 1164, 127 L. Ed. 2d 500, 1994 U.S.
[10]参见:(2017)粤73民终85号民事判决书、(2011)一中民初字第1321号民事判决书。
[11] 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J].知识产权,2017(0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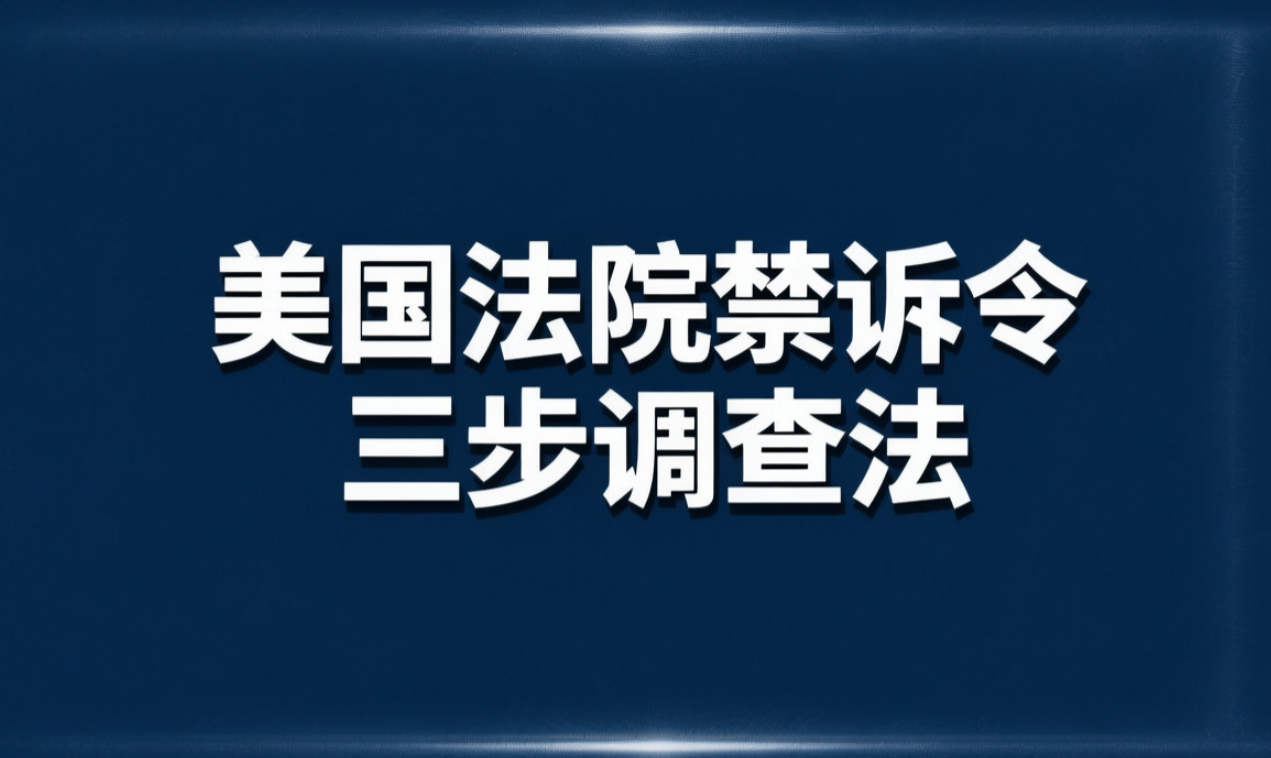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上一篇
上一篇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