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专利
专利 -
 商标
商标 -
 版权
版权 -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
 反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 -
 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 -
 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
 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 -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律师动态
更多 >>知产速递
更多 >>审判动态
更多 >>案例聚焦
更多 >>法官视点
更多 >>裁判文书
更多 >>近年来,由于恶意注册和囤积商标的现象愈演愈烈,商标行政和司法政策调动一切法律工具进行重点打击。面对形式多变、隐蔽而又巧妙的抢注和囤积行为,一直以来法律工具都显得有些供给不足。
《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不良影响条款”[1]曾经被作为工具使用,后来,实践中也存在利用《商标法》第7条诚实信用一般条款打击恶意注册的情况。但《商标法》第7条毕竟为一般条款,其基本精神已经体现在《商标法》的具体条款中,单独适用存在障碍,因此后来司法实践采用了在诚信条款外再附加《商标法》第44条第1款来打击恶意注册的思路。例如,在“XIAOMI”案中,法院指出,行为人借助他人知名品牌进行不正当竞争或牟取非法利益的意图,其行为不仅有悖诚实信用原则,而且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有损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了商标法第44条第1款之规定。[2]
《商标法》第44条第1款后来便慢慢地成为打击批量抢注的主要法律工具之一。然而,《商标法》各条款的适用均有边界和适用要件,适用不当就会导致错伤和误伤,运用一切可利用的法律工具打击商标恶意注册和囤积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实施中也出现了偏离条款适用初衷,以打击恶意为名伤害在市场中已经使用多年商标的情况。绝对条款的适用急需纠偏,以维护稳定的商标注册秩序和正常的市场竞争。
从审查审理实践呈现出来的不当适用绝对条款的发展轨迹来看,最早涌现的是不良影响条款的滥用,对此,曾有人批判指出,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不良影响的调整范围应被严格限制与损害“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这一情形相近的而又无法用其他条款规制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根据体系解释,该条款作为商标绝对禁止注册条款,规范的应当是最需要严厉禁止的一类商标。因此其调整范围就不应当扩张到其他相对事由条款的适用范围,从而打破商标法的逻辑结构,造成法律适用的错位。[3]后来行政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逐渐认识到不良影响条款主要针对的是标志而非行为,且不良影响必须是有关标志或者构成要素可能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才能适用。[4]
《商标法》第44条第1款曾被用来处理特定利益主体的权益保护,[5]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第24条明确:以欺骗手段以外的其他方式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不正当手段”,但实践中仍存在以该条款保护特定权益主体权益的情况,特别是市场主体因部分商标存在恶意抢注而其他正当注册并使用多年的商标被牵连宣告无效的案件越来越多。
近几年,不良影响条款和不正当手段注册条款的错用还没有完全过去,又出现了另一种让人担忧的现象:以打击恶意注册和商标囤积之名,依据《商标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商标显著性条款、《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的欺骗误导条款宣告使用多年的商标无效。绝对条款的适用因不受五年争议期间的限制,且欺骗误导条款又属于禁用条款,其适用后果对商标注册人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这导致市场主体谈绝对条款“色变”,遭绝对条款之扰困顿不堪。
本文以为,以显著性条款以及欺骗误导条款宣告注册商标无效必须遵循其各自严格的适用条件,在商标注册后使用多年且已经形成一定市场影响的情况下,依据绝对条款宣告商标无效尤其要慎之又慎。下文就这两个条款适用的边界作以厘清,以期将目前实践中频现的绝对条款错用拉回正途。
一、《商标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只适用于标志“仅”且“直接”描述商品特点的情形
我国《商标法》第11第1款第2项规定了“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志,不具有内在显著性,在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之前不能获得商标注册。从文面表述来看,该规定规范的是“仅”且“直接”表示商品特点的标志,这也即意味着,如果标志不是“直接”表示商品特点,而是存在间接或者含蓄的联系,就不适用此条款;或者,除了直接表示商品特点的标志,标志还有其他构成要素,也即不是“仅仅”由直接表示描述商品特征的标志构成的,也不适用此条款。这是从该规定的文面表述中能够且应该解读出来的条文应有之义。
另外,从规定的渊源来看,“仅”且“直接”的叠加构成要件也符合其公约层面的来源规定。我国《商标法》第11条第1款的规定源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称《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五第(二)款第(2)项规定的内容,即排除“缺乏显著特征的商标,或完全是用在商业中指明(designate)商品种类、质量、数量、用途、价值、原产地或生产日期的符号、标记所组成的商标,以及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现代语言或正当商务实践中惯用的符号标记所组成的商标”,其中第11条第1款第2项对应的是“完全(exclusively)是用在商业中指明(designate)商品种类、质量、数量、用途、价值、原产地或生产日期的符号、标记所组成的商标”,“完全由……组成(consist exclusively of)”的表述与我国《商标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中“仅”的表述含义是一致的,“指明(designate)”则对应“直接”描述,由此可见,《商标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源自《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五第(二)款第(2)项规定,强调只有且完全由描述性标志构成、再无其他要素的标志不具有内在显著性。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典型案例来看,在适用《商标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时,司法判决也强调同时满足“仅”和“直接表示”两个要件,如果并非属于“仅”“直接表示”,就不属于不得作为商标注册的范围。那么,如果标志除了直接描述性标志还有其他构成要素,则不适用此规定。例如,针对“沩山牌及图”商标的显著性问题,最高法院指出:判断争议商标是否应当依据《商标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予以撤销时,应当根据争议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从整体上对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进行判断,不能因为争议商标含有描述性文字就认为其整体缺乏显著性。本案争议商标由沩山牌文字、拼音及相关图形组成,并非仅由沩山文字及其拼音组成,其商标组成部分中的图形亦属该商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沩山牌及图”商标可以维持在茶叶商品上的注册和使用。[6]又如,在“肾源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指出,商标标识或者其构成要素暗示商品的特点,但不影响其识别商品来源功能的,不属于《商标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情形。最高法院认为,在该案申请商标中,“肾源春”三个字的组合虽然能够暗示商标所指定使用商品的功能、用途等特点,但系臆造词汇,相关公众需要通过想象、演绎等方式才能建立申请商标标识含义与其指定使用的商品所具有的功能之间的关联性,不影响申请商标的识别商品来源功能。“冰糖蜜液”四个字虽存在直接描述了商品的原料的问题,但其与“肾源春”三个字的组合,不属于仅直接表示商品原料的情形。申请商标从整体上进行判断,具有识别和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具备作为商标标识使用的显著性。[7]
另一方面,如果标志不是“直接”描述性标志,也不适用《商标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对于“直接”描述性标志的理解遵循客观的标准,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商标法释义》以及《商标审查及审理指南》中关于《商标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的解释中所举例子都明确体现了这一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撰的《商标法释义》中的例子如将“纯净”作为饮用水的商标,将“柴鸡”作为调味品的商标,将“安全”作为漏电保护器的商标,将“50kg”作为大米的商标,将“蜡染”作为布的商标。[8]在《商标审查及审理指南》中,对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功能、用途的例示,如指定使用在食用油上的“纯净”、指定使用在香烟上的“50支”,指定使用在诉讼服务上的“法律达人”等。从这些例子中都可以看出,这些标志相对于指定使用的商品和服务都明显具有直接描述的性质。如果标志和指定商品和服务具有间接联系,或者联系关系较远,就不属于具有直接描述性的标志,也就不属于本条项规范的范畴。像注册在计算机硬件、软件、在线游戏、电子商务、网站维护等商品或者服务上的“歌单”这种生造词就不具有直接描述性,具有内在显著性,不属于《商标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情形;而对于注册在培训、教育、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眼镜等商品或服务上的“歌单”商标,商标本身与商品或服务的关系更远,更不应当用《商标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予以规制。
当然,与指定商品或服务具有间接联系的暗示性标志,其内在显著性比较弱,因为其本身与商品或者服务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间接联系而使得标志能够较快地与商品或者服务建立对应关系,让相关公众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市场认知,但其本身不直接描述商品或服务的特征,标志的排他使用给注册人带来的竞争固有优势有限,故而商标法并不在源头上否定其注册可能性,其本身属于具有内在显著性的标志,可以不经使用获得显著性即注册为商标。在“视力健”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曾指出,如果诉争商标属于暗示性标志,则其虽然显著性相对较弱,但仍属于具有显著性的情形。“视力健”商标指定使用在第5类眼药水等商品上,相关公众虽可以理解出该商标的含义,但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系对该含义的常规表述方式,不同人对该含义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故诉争商标属于暗示性标志。[9]
另外,在一些新创词作为商标时,新创词的构成往往取自现有语汇,与指定商品或者服务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具有一定程度的描述意义,但只要新创词本身不具有直接描述性,其作为商标就具有内在显著性。例如,在“财付通”案中,腾讯公司申请的“财付通”商标,指定使用在第36类“网上银行、金融服务、不动产代理、募集慈善基金、信托、金融管理、保险”服务。尽管涉及“财”的“支付”,且“通”可解释为“财付通畅”“财付通道”等含义,显然对指定使用服务的特性有一定的描述。但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两审法院[10]通过区分“暗示性标志”和“直接描述性标志”,认为“财付通”三个字并未形成对上述服务的内容、质量等特点的直接描述,而仅仅属于具有一定暗示性含义的标志。
当然,暗示性标志本身内在显著性不强,对于那些介于暗示性和描述性标志之间的标志,基于从严掌握商标注册申请审查政策可以不给与注册,但是,对于已经获得注册的商标,特别是已经投入商业使用的商标,则不应再予以无效宣告,这既不符合商标法律制度中的显著性要件的基本要求,伤害商标注册的稳定性,也对已经形成的市场秩序带来破坏。比如在“兰州牛肉拉面”案件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仅以争议商标缺乏固有显著性,即将持续使用较长且规模较大的商标予以宣传无效,势必将造成相关公众已经形成的基于该商标对具体商品品质、特点、声誉对应认知的损耗,并不有利于商标注册制度的健康发展”[11]。再比如对“歌单”商标而言,“歌单”商标的注册、使用已经超过十年,这期间企业围绕“歌单”推出了大量的产品、投入巨大。这种情况下,依据《商标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宣告“歌单”商标无效,不利于维护商标秩序的稳定性、也会破坏业已形成的市场秩序。当然,这些弱显著性商标注册后在进行商标维权时,可以科学界定商标权的保护范围,对暗示性标志的排他范围进行适当限缩。
二、《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需要以公众误认为结果要件且仅适用于损害公共利益的严重情形
(一)《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欺骗误导条款的适用必须以导致公众误认为结果归依,在不发生公众误认的情况下不应该予以适用。
这首先是基于《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规定的文面表述,即“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从条文规定来看,适用该欺骗误导条款必须满足两个要件:第一,带有欺骗性;第二,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
其次,从欺骗误导条款的历史演变来看,《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规定由2001年《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修改而来。2001年《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夸大宣传并具有欺骗性的。从该条的历史变迁可见,修法后,除满足“欺骗性”要件外,该项还特别明确强调“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要件,二要件缺一不可才构成《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规定适用的情形。这也在《商标审查及审理指南》规定中所重申,即本条中的“带有欺骗性”是指标志对其指定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来源作了超过其固有程度或与事实不符的表示,容易使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来源产生错误的认识。如将“健康”“长寿”标志指定使用在“香烟”商品上;将“万能”标志指定使用在“药品”商品上。如果公众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等不会对标志指定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来源产生误认的,不属于该项规定的情形。《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在欺骗性的认定上也规定,公众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等不会对诉争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属于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七项规定的情形。由此可见,《商标法》欺骗误导条款的适用需满足两个构成要件:第一,带有欺骗性,即商标对其指定使用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作了超过其固有程度或与事实不符的表示;第二,容易使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错误的认识。特别是《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还用逆否命题的形式强调了公众误认要件的必要性。
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判决明确指出,根据公众的认知,如果不产生欺骗误导的后果时,则不适用欺骗误导条款的规定。例如,在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诉争商标由汉字“小米”构成。“小米”本身为一种常见的谷物,与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水(饮料);矿泉水配料;制啤酒用蛇麻子汁”商品差异明显,社会公众基于生活常识,通常不会因诉争商标中含有“小米”一词而认为上述商品含有“小米”成分,从而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认。故诉争商标核定使用在上述商品上不具有欺骗性,未违反2013年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的规定。[12]再比如在“竹酿春”案件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对于“欺骗性”,应当“应当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水平及认知能力出发,结合指定使用的商品进行界定”,“竹酿春”用于鸡尾酒等商品上“不会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功能等特点产生误认,不具有欺骗性”[13]。对于经过长期使用的商标,比如“歌单”等,其是否具有欺骗性,应当考虑客观的实际使用效果。对于这类使用超过10年的商标,如果客观上没有任何欺骗性的后果,应当慎用《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宣告该商标无效。
(二)《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欺骗误导条款仅适用于损害公共利益较严重的情形,如果公共利益或者公共秩序没有受到损害就没有必要适用。
首先,从渊源来看,《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来源于《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五第(二)款第(3)项规定的内容,即“除下列情况外,对本条所适用的商标既不得拒绝注册也不得使注册无效:……商标违反道德或公共秩序,尤其是具有欺骗公众的性质。这一点应理解为不得仅仅为商标不符合商标立法的规定即认为该商标违反公共秩序,除非该规定本身同公共秩序有关。”《巴黎公约》的相关规定非常明确,“欺骗公众”所指向的情况必须与公共秩序的违反有关,指的是违反道德或公共秩序的情况,当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特定主体的权益或者公共秩序、公共利益没有受到损害时,则不应该适用此项规定进行干预。
其次,从体系解释和逻辑解释的角度来看,《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位于第10条第1款之下,其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应当与第10条第1款其他条项保持一致。《商标法》第10条第1款为商标禁用条款,其规制的都是违反道德或公共秩序的较为严重的行为,违反此项规定的标志既不能获得注册,也禁止作为未注册商标使用。由此可见,《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也意在规制违反道德或公共秩序的较为严重的行为。据此,在适用第10条第1款第7项欺骗误导条款时应当遵循两个原则:第一、第10条第1款第7项的适用应当体系化地与第10条第1款其他项保持平衡。必须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为违反道德或公共秩序的较为严重的行为,不能过分降低其适用门槛或者随意适用,否则就会造成第10条第1款各项之间的适用失衡。第二、基于第10条第1款第7项的立法目的,其是法律赋予公权机关保护公共利益的条款,但商标权本质上是私权,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在适用该条进行公共利益保护和公共秩序维护时,应当秉承谦抑、宽松的态度,遵循“最小介入”原则,保持对市场正常经营的尊重和对市场干预的最大克制,否则将会不正当地限制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限缩其创意空间。
目前,在适用欺骗误导条款宣告商标无效案中,审查和审理机关经常会犯的错误是仅仅从标志与指定商品或服务的关系就直接推断出公众会上当受骗,不考虑商标使用的可能场景和公众的正常认知,更不追问欺骗误导条款要规制的究竟是何种情形下的“欺骗”。例如,在“肾源春”案中,申请商标是由“肾源春冰糖蜜液”七个汉字上下排列组合而成的文字商标,指定使用于“原料药、药酒、膏剂、医用营养饮料、医用营养品”等商品上,乍一看,商品如果是药酒的话,冰糖、蜂蜜的使用会有误导。但是,如果我们结合标志的使用以及消费者选择商品的具体场景,很容易就会意识到事实上消费者很难产生错误认识。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再审判决中所指出的,其实,仅从申请商标标志本身,尚不足以认定申请商标使用在指定商品上将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料、成分等特点产生错误认识,难以认定构成对公众的欺骗。[14]
另外,从欺骗误导条款规制的最终目的来看,其所针对的主要是标志本身故意夸大商品或服务的功能、作用[15],或者标志本身表示了商品本身不具有的质量或者功能等,目的都是为了美化商品或者服务,并进而诱导消费者在错误的认识下进行消费,出于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防止利用商标欺骗消费者,[16]典例如用在香烟上的“健康”、用在药品上的“万能”。因此,对于那些从本质上并未进行夸大、美化,或者即使有夸大、美化的因素但根本不会导致消费者受骗并进而被刺激消费的情况,其实并不需要启动欺骗误导条款进行干预,此种情况下也并没有产生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的损害。
总之,在依据绝对条款对已经注册并使用多年的商标宣告无效要慎之又慎,避免运用毁灭性后果的条款不当干预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和已经形成的市场秩序,特别是依据禁用性条款的欺骗误导条款做出无效宣告时更要谨慎,切忌用简单机械的推导关系就确定误导公众成立,商标使用于商品或服务上必然会有具体场景,而且一个使用多年的商标已然经过了市场的检验,如果有欺骗误导的后果应该早已经在市场中反映并显现,在没有产生了误导欺骗后果的确切实证的情形下公权力介入干预不仅仅是多余之举,更是对正常市场秩序的强破坏。
注释
[1] 杜颖:《商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版,第28页。
[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京行终656号。
[3] 参见马一德:《商标注册“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载《中国法学》2016 年第 2 期,第229-230页。
[4] 参见杜颖:《〈商标法〉“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探析——基于“MLGB商标无效宣告案”的思考》,载《电子知识产权》2017年第5期,第79页。
[5] 参见李琛:《论商标禁止注册事由概括性条款的解释冲突》,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8期,第4页。
[6]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1)行提字第7号。
[7]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249号。
[8] 参见朗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9]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京知行初字第5848号。
[10]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6)京行终1298号。
[11]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京行终6256号。
[1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3)京行终688号。
[1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京行终6121号。
[14]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249号。
[15] 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16] 扈纪华、孙晓青(主编):《新商标法释解与操作实务》,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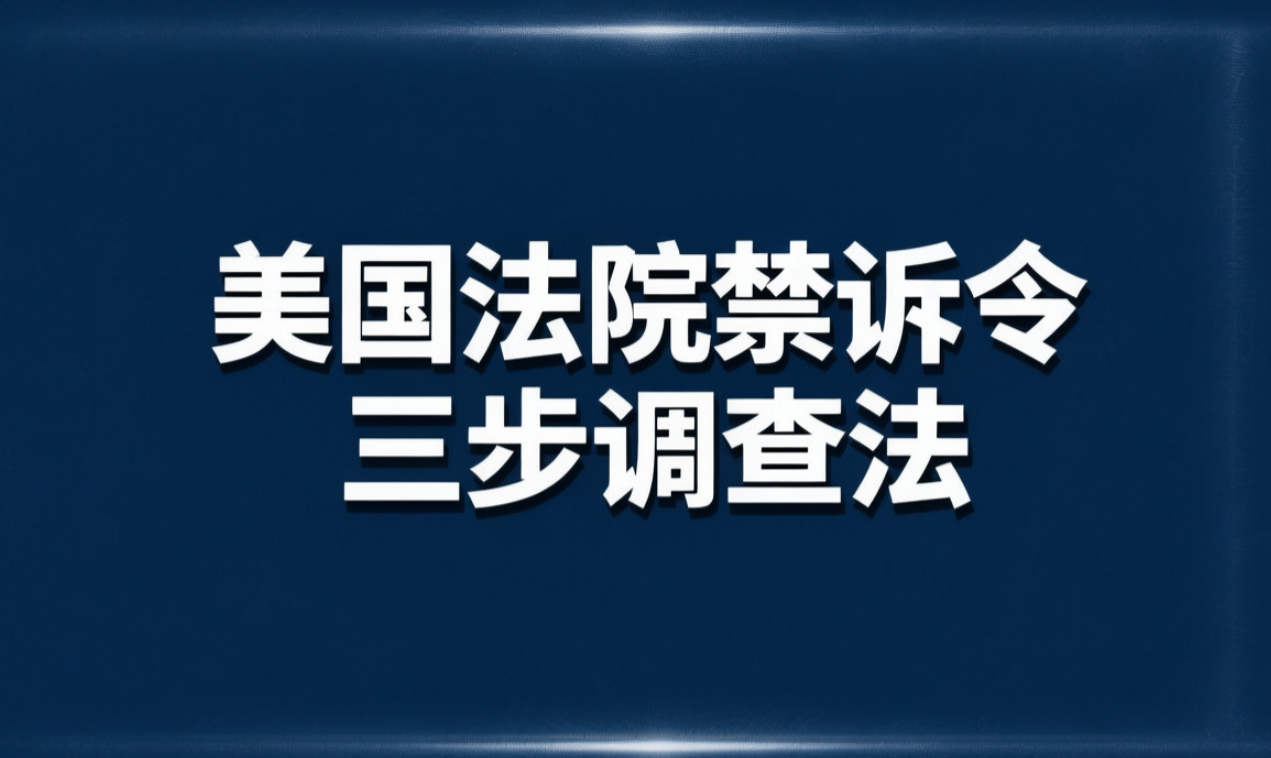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上一篇
上一篇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