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专利
专利 -
 商标
商标 -
 版权
版权 -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
 反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 -
 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 -
 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
 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 -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律师动态
更多 >>知产速递
更多 >>审判动态
更多 >>案例聚焦
更多 >>法官视点
更多 >>裁判文书
更多 >>摘要
《著作权法》第三条对于作品类型做了分类,每种类型对应特定的表现形式。作品分类在立法上的规范意义不仅在于示例,更在于确定特定作品的保护规则。不同类型的作品在权利归属、保护期限、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等方面可能对应不同的规定。作品保护范围虽然不限于具体的表现形式,但表现形式在一些情况下会对保护范围产生影响。因此,在作品侵权认定中,需要考虑实质性相似部分所对应的作品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其权利归属、保护期限、保护范围等。
关键词:著作权法;作品类型;保护规则;侵权认定
一、问题的提出
作品类型与作品权利归属、保护期限、保护范围等著作权保护规则密切相关,但对作品保护的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我国版权理论界和实务界尚存在一些分歧。特别是关于作品类型与保护范围的关系,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类型作品以不同表达方式来划分,作品的独创性体现在该作品的表达中,并以此确定作品的保护范围。在该观点看来,判断是否侵权,首先应对涉案的作品类型作出认定;再对被诉侵权作品是否使用了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表达作出认定。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作品类型的规范意义在于对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形式进行列举,作品类型不应起到限制受保护作品保护范围的作用。在侵权判定过程中,应当坚持作品表达整体保护观,综合考虑作品采用的各种表达形式,将外在表达和内在表达均纳入考量范围,以被告是否利用了作品的实质部分作为侵权判断的根本标准。
基于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出,对作品类型与著作权保护范围关系的不同认识,对于侵权认定的基本思路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基于此,本文从作品类型的规范意义、作品表现形式与作品保护范围、作品类型与侵权认定三个角度出发展开论证。
二、作品类型的规范意义
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包括:(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四)美术、建筑作品;(五)摄影作品;(六)视听作品;(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八)计算机软件;(九)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对于该条款可从两个角度理解:其一,该条款中对作品的具体类型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二,其改变了修订之前《著作权法》中采用的作品类型封闭的做法,采用了作品类型开放的模式。也就是说,理论上讲,除了该条款所列举的八种作品类型外,其他的智力成果如果符合作品的条件,亦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
对于作品类型进行明确规定,并非我国著作权法的特殊做法。事实上,很多国家的立法均有类似规定。其中,美国《版权法》列举了8类受保护的作品类型;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列举了14类作品类型,德国《著作权法》则规定了7类作品类型。虽然作品类型的规范意义之一在于对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形式进行示例,但由此认为作品类型化的意义仅限于示例性却是不全面的。作品的分类除了有利于提供找法便利、减轻解释负担、便于作品登记,更重要的是,它与权利内容、权利归属、保护期限、权利限制等保护规则密切相关。
在权利内容方面,《著作权法》第十条对某些作品类型规定了特别的权利,而其他作品类型则无相应的权利。其中,只有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人才享有出租权;展览权只存在于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之中;而放映权仅限于美术、摄影、视听作品,其他作品不产生放映权。不仅如此,针对一些权利的侵权行为,亦只有特定作品类型可能涉及。比如,只有视听作品可能构成对摄制权的侵害,侵害翻译权的行为则只可能发生在文字作品之间。
在权利归属方面,《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因此,通常情况下,作品的各项权利由作者享有。但鉴于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特殊性,法律将该类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分配给了制作者。而对于软件作品的权属,《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自然人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任职期间所开发的软件有该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软件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权利,自然人只能获得奖励。
在保护期限方面,《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中不仅从区分自然人或者法人、非法人组织的角度,对作品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作出了一般规定,且对于视听作品的保护期,亦特别规定了其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著作权法》虽然并未明确将实用艺术作品规定为作品类型之一,但司法实践中通常把实用艺术作品当作美术作品给予保护,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大大延长了这类作品的保护期限。但在《伯尔尼公约》看来,基于实用艺术作品的特殊性,这类作品的保护期限应当短于一般作品,因此将其简单地纳入美术作品是不妥的。
在权利的限制方面,《著作权法》亦对某些类型作品作了特别的规定。《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十二项具体的合理使用情形,其中第(十)项为“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第(十一)项为“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已经发表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针对第(十)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进一步规定,“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是指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社会公众活动处所的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对前款规定艺术作品的临摹、绘画、摄影、录像人,可以对其成果以合理的方式和范围再行使用,不构成侵权”。基于该规定可知,《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十)项中所称的“艺术作品”具体是指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作品。也就是说,该项权利限制对应于特定的作品类型。至于第(十一)项“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则仅指文字作品。对此,在司法实践中已有相关认定。
在金鹰卡通公司诉央视国际公司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金鹰卡通公司主张其是动画片《翻开这一页》的著作权人,央视国际公司未经金鹰卡通公司合法授权,在其经营的“UYNTV”安卓手机客户端上提供该作品的在线播放服务,使用户能够在线观看相应内容,该行为侵害了金鹰卡通公司对该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针对这一主张,央视国际公司的抗辩理由之一是这一使用行为属于2010年《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合理使用行为,即属于“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的行为。但法院并未支持这一观点,而是认为,2010年《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有关将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的规定,仅限于汉语言文字作品,但涉案动画片《翻开这一页》并非文字作品,因此被诉行为并不属于合理使用。
此外,在法定许可部分,同样针对特定作品类型做了相应规定。《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为实施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的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图形作品”。《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利用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即“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
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计算机软件。《伯尔尼公约》第2条列举的作品类型中虽然并不包括计算机软件,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4条规定,“计算机程序作为《伯尔尼公约》第2条意义下的文字作品受到保护。此种保护适用于各计算机程序,而无论其表达方式或表达形式如何”。但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把计算机软件当作文字作品,而是作为一类单独的作品,并由国务院制定《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专门保护计算机软件,从而使其与文字作品在保护规则上存在区别。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某些作品类型与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规则密切相关。可见,作品分类在立法上的规范意义除了例示外,还在于确定特定作品的保护规则。因此,正确区分作品类型,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都有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音乐喷泉案中,原告把“音乐喷泉”视为电影作品,一审法院认定为是“其他作品”,而二审法院则判定为美术作品。根据上述分析,对“音乐喷泉”作品类型的不同认定,其法律适用必然将会带来很大的差异。
三、作品表现形式与保护范围
《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因此,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须以一定形式予以表现。换言之,作品应是可被客观感知的思想或者情感的外在表达。这种外在表达包括文字、音符、数字、线条、色彩、造型、形体动作等方式。与此相应,也就有了文字作品、音乐作品、美术作品、舞蹈作品等不同的作品类型。“以一定的形式表现”的法律意义之一在于“确定思想表达的客观样式,根据其客观表现形式进行作品分类。诸如文字著述、舞台演绎、音乐表达等”。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明确列举的八种作品类型基本上均是以作品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比如,文字作品以文字形式表现,音乐作品的基本表现手段是旋律和节奏,美术作品以线条、色彩等来呈现,视听作品则借用一系列滚动的画面来传达,等等。
作品作为一种表达,通常以特定的样式或者形式体现,并不意味着作品上的各项权利仅及于作品的最终样式或者形式,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不仅指文字、色彩、线条等符号的最终形式,当作品的内容被用于体现作者的思想、情感时,内容亦属于表达,受著作权法保护。将文学剧本改编摄制成电影,作品从文字作品变成了视听作品,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剧本中的情节、人物关系等内容被电影所使用,如果该电影的制作是未经剧本著作权人许可的,则构成侵权。至少对于部分作品而言,与“思想”相对应的“表达”不仅仅包括“形式”,也包括“内容”。因此,笔者认为,那种“已经纳入特定类型的具体作品,受保护的表达应以该类作品定义中规定的表现形式所限定者为限”的观点值得商榷。作品的表现形式与作品的表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虽然作品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作品的最终样式或者形式,但思想表达的样式或者说作品的表现形式客观上会对作品的表达产生影响,从而对作品的保护范围带来相应的限定。也就是说,表现形式作为对作品的表达手段或外在表达,与内在表达并非毫无关联,而是密切相关。
以美术作品为例。美术作品是造型艺术,其保护范围围绕着造型本身来确定。在法蓝瓷工艺产品案中,原告认为被告生产的茶壶等产品与原告产品相比均属于日用艺术陶瓷作品,主要设计元素一致,均为白底、红色金鱼、绿色水草,且主题图案设计和布局、色彩组合、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法相似,尤其是金鱼尾巴扬起、红白色相间处理的手法等都无实质差别。因此,被告产品构成对原告作品的侵权。但法院则认为:虽然两者的产品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异。相同之处主要是设计主题、思路、位置关系和动植物形象等元素,这些相同之处尚未使两者的产品达到实质性相似的程度,被告的行为没有超出应有的界限。本文认为,法院对此案的结论是正确的。美术作品是以线条、色彩等表现的造型艺术作品,对美术作品的侵权认定应以艺术造型方面的实质性相似为前提。
将美术作品与文字作品进行对比,则可以进一步解释这一问题。“图画、油画……是与文学作品相区别的……一类不同的智力表现形式,它们是用来静态观看和欣赏的,而不是像文字作品那样用来阅读,或像戏剧作品或乐曲那样用来演奏的”。也就是说,图画、油画等美术作品与文字作品在表现形式及用途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它们在各自表达范围上的差异。无论如何,人类的语言均无法精确地描述达到一定复杂程度的绘画。在人民法院早期的有关著作权诉讼、商标权诉讼的民事判决书中,对案件涉及的美术作品或图形商标大多使用文字来描述,但受文字所限,判决书几乎不可能准确地表达出其所描述的美术作品或图形商标,读者读了只能是云里雾里。基于这一原因,近些年改为在判决书中直接附上美术作品或图形商标。这一情形说明,用文字描述美术作品、图形商标时,美术作品、图形商标中的美感(即表达)并没有体现在文字描述中。
但与之不同的是,用美术作品展现文字作品,则有可能构成侵权。比如,漫画家使用他人小说中的全部故事情节和人物等内容绘制出一套漫画,则可能是侵权的,原因在于小说的表达在一系列漫画中往往能够得以重现。但如果画家只是根据小说中的某个情节绘制一幅画,比如根据《水浒传》关于武松打虎一节制作武松打虎画;根据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对林黛玉形象的文字描述、刻画绘制林黛玉肖像,很有可能因为武松打虎画、林黛玉肖像并没有使用小说的表达,而不构成侵权。
将舞蹈作品与文字作品相比,亦存在类似情形。舞蹈作品是通过连续的动作、姿势、表情等表现思想情感。因此,舞蹈作品即使是根据某个故事设计的,但由于受到表现手法的限制,也只能将故事以非常抽象的身体语言向观众传达,难以使观众较为充分地了解该故事的具体情节。相反,用文字来传达舞蹈作品也存在同样的障碍,读者难以从文字中感知舞者具体的动作、姿势、表情。
从上述分析可见,虽然对作品的保护不仅及于最终表现形式(外在表达),在很多时候也及于内容(内在表达),但具有独创性的内在表达的再现无疑会受到作品表现手段(形式)、作品类型的限制。在一些情形下,特定的独创性内在表达只能在特定的表现形式、特定类型的作品中才能再现。
四、作品类型与侵权认定
有观点认为,表现形式可以作为一类作品区别于其他类作品的特征,但是这种区别特征不能作为划定特定类别作品中受保护表达范围的依据。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认定中应当秉持表达的“整体保护观”。以原告受保护的作品为基点,考察被告行为是否落入原告作品的保护范围。类型归属不应成为限定特定作品中受保护表达范围的羁绊。根据作品表达整体保护观,应关注的是被控侵权人所利用的部分内容是否构成原告作品整体表达的实质部分,比如,对舞蹈作品、杂技作品、戏剧作品、视听作品等拍摄剧照或者进行截图的,应以被截取的部分是否构成原告作品整体表达的实质部分为判定侵权的基本思路。还有观点认为,在判断是否侵权时,应判断被控侵权作品与原作品之间的相似部分是否构成来源于原作品的独创性表达,而无需考虑实质性相似部分是否构成原作品的作品类型。
如上所述,著作权法规定作品的类型并非只有示例作用。当然,如果著作权法没有对某些作品设立特定的保护规则时,则区分这些不同作品类型似乎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前文所述,著作权法针对不同的作品类型存在很多不同的保护规则。此种情况下,在侵权比对中区分正确的作品类型有着重要的意义。毕竟,这些保护规则往往涉及作品的权利归属、权利内容、保护期限、权利限制等。
这一问题在电影作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电影通常是由小说、电影剧本、摄影、音乐、美术作者以及导演等众多创作者集体创作的综合性艺术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制作者享有电影作品的各项权利,电影作品中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权利。因此,在以电影作品为诉讼标的的侵权案件中,必须根据当事人主张的被诉侵权行为使用的是电影连续画面(电影作品),还是电影剧本、音乐作品、美术作品等来进行审理并分别适用法律规则。相应地,如果被诉侵权作品既涉及电影作品,又涉及电影剧本,同样需要分开进行评述。
比如在琼瑶诉于正案中,琼瑶主张其为电视剧剧本及同名小说《梅花烙》的著作权人,被告于正未经许可,擅自采用涉案作品核心独创情节进行改编,创作电视剧剧本《宫锁连城》,湖南经视公司、东阳欢娱公司、万达公司、东阳星瑞公司共同摄制了电视剧《宫锁连城》,上述行为均涉及侵权。该案中,虽然《梅花烙》已被拍摄为电视剧,但法院仍认为,琼瑶涉案小说及剧本的作者,是上述文字作品的著作权人。针对被诉侵权剧本,法院认为于正接触了涉案作品的内容,并实质性使用了涉案作品的人物设置、人物关系、具有较强独创性的情节以及故事情节的串联等,改编形成新作品《宫锁连城》剧本,上述行为超越了合理借鉴的边界,构成对涉案作品的改编,侵害了原告基于涉案作品享有的改编权。针对涉案电视剧,法院认为,电视剧《宫锁连城》是依据剧本《宫锁连城》摄制而成的,在剧本《宫锁连城》系未经许可对原涉案作品改编而成的情况下,未经许可摄制的电视剧《宫锁连城》侵害了原告的摄制权。
在奥特曼美术形象案中,原告主张其从《迪迦奥特曼》系列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处获得了对该影视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等,因此,对该影视作品中的“迪迦奥特曼”角色形象享有上述权利,但被告未经授权,擅自将该人物形象用于生产、销售玩具,该行为构成侵权。针对原告这一主张,法院认为虽然2010年《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二款仅明确了“剧本”“音乐”两种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但一个著名的角色形象亦可以独立于特定的作品而活在公众的想象中,因此,迪迦奥特曼角色形象构成独立于影视作品、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虽然2010年《著作权法》将电影作品的权利整体赋予制片者,但被控侵权商品将“迪迦奥特曼”角色形象复制在其商品上,是对影视作品中可单独使用的作品的单独使用,而非对影视作品的整体使用。原告是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不能仅仅依据其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身份就来对影视作品中的角色形象主张权利,其应举证证明其享有奥特曼美术作品的著作权。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法院对当事人关于其为电影剧本、角色形象著作权人的主张分别作出裁判。即如果把剧本、角色形象都当成电影作品的“实质部分”,按照2010年《著作权法》的规定,则作品的各项权利应归电影制片者所有,而非上述案件中的原告,有的案件将会有不同的结论。
实践中,在涉及电影作品的案件中,另一较为典型的问题在于,当他人未经许可将电影改编为话剧时,侵害的是文字作品著作权人还是电影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在白先勇诉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案中,原告白先勇系小说《谪仙记》的作者。1989年,经原告许可,原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小说《谪仙记》改编为电影《最后的贵族》并于同年上映。2013年,被告艺响公司筹划将电影《最后的贵族》改编为同名话剧,为此取得了制片方被告上影集团的授权,但未能获得原作品作者即原告的许可。在此情况下,被告艺响公司、君正公司进行改编活动并演出6场。原告认为上述三被告共同侵害了原告所享有的《谪仙记》作品的改编权、署名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针对原告上述主张,法院认为: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对其拍摄的电影《最后的贵族》享有著作权,但该电影属于演绎作品,将该演绎作品改编为另一种作品形式即话剧并演出,需要同时取得原作品和演绎作品著作权人许可。被告艺响公司、君正公司未经原作品作者即原告的许可,将电影作品《最后的贵族》改编为同名话剧并进行演出,侵害了原告享有的对其小说作品《谪仙记》的著作权。法院之所以采用这一观点,原因在于改编的话剧同时使用到了电影作品以及作为文字作品的电影剧本的内容,因此,其需要同时从上述著作权人手中获得许可。而如果依据前文提到的整体保护观,将剧本内容作为电影的实质部分进行考虑,则可能会得出跟判决不同的结论。
五、结语
作品分类在著作权法上的规范意义并非仅仅是为了例示,还在于确定特定作品的保护规则。虽然作品通常以其表现形式分类,但保护范围不限于作品的最终样式或者外在形式,还包括内在表达。当然,表达的样式或者说作品的表现形式客观上也会对作品的内在表达产生影响,从而为作品的保护带来相应的限定。鉴于不同类型的作品在权利归属、保护期限、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等方面可能对应不同的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的侵权认定需要考虑实质性相似部分所对应的作品类型,进而确定该部分作品的保护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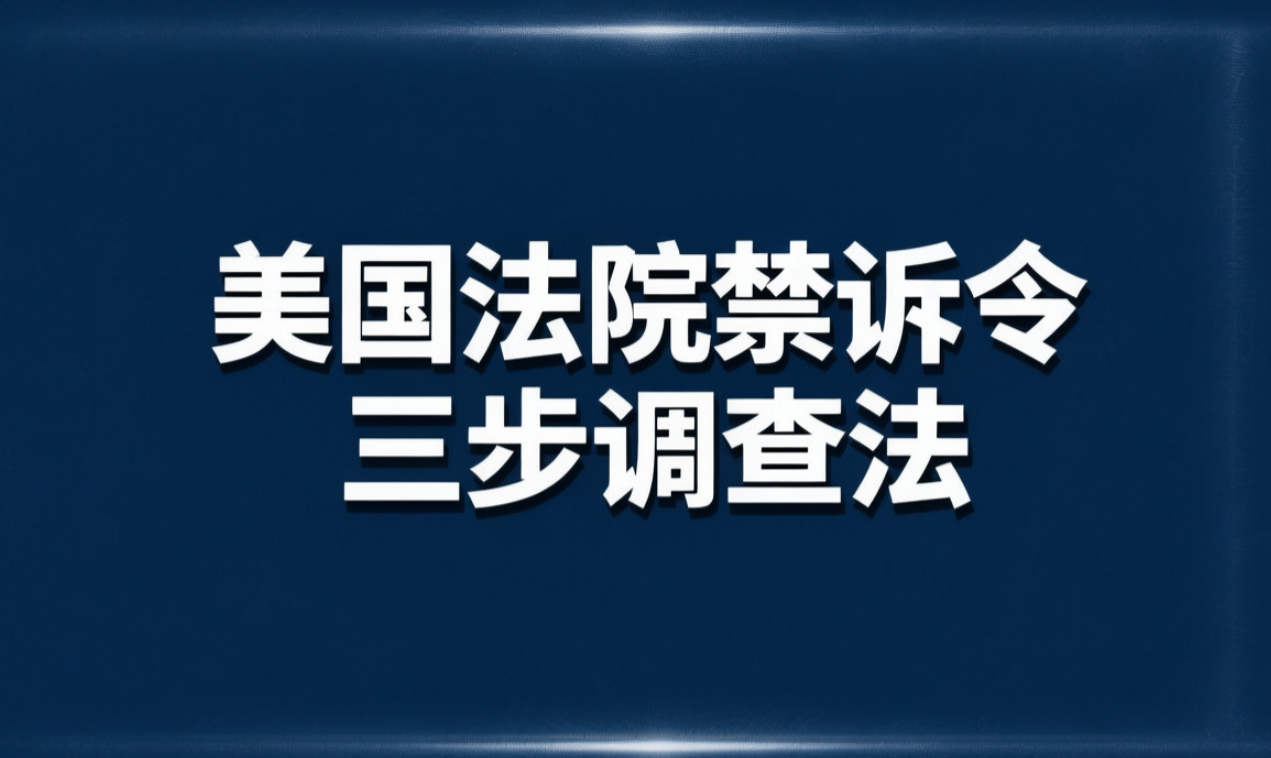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上一篇
上一篇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