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专利
专利 -
 商标
商标 -
 版权
版权 -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
 反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 -
 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 -
 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
 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 -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律师动态
更多 >>知产速递
更多 >>审判动态
更多 >>案例聚焦
更多 >>法官视点
更多 >>裁判文书
更多 >>内容提要
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的绝对事由需要在立法上进行必要的完善,回归宣告无效针对不正当注册的原意,确保商标核准注册与无效宣告程序中绝对事由的对应性和同一性,重点是尽快去除“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的独立无效事由。在既有法律规定下,绝对无效事由的适用应当保持必要的谦抑,避免适用上的扩大化或者扭曲化。当前的商标确权实践应当突出强调实际使用的优越地位,避免过于强调商标申请注册时的“原罪”而无视实际使用的现实,导致无效宣告“舍本逐末”“缘木求鱼”;要真正认真对待两种事由的法律界限,尊重其区分价值,避免动辄以绝对事由变相发挥保护在先权利的相对事由功能,防止以绝对事由为名变相扩展在先权利,维护权利保护与商标秩序的平衡。
关 键 词
注册商标无效宣告 绝对事由 相对事由 非使用性批量注册商标 欺骗手段 其他不正当手段
商标法不仅是以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生、变更、消灭和保护为主线条的权利法,还关乎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因而又有一定程度的公法介入。特别是,我国目前的商标注册实践由行政主导,绝对事由是商标授权确权机关(包括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以及后续的司法审查法院)控制商标授权确权的基本路径和主要抓手。当前商标注册实践中商标授权确权机关通过绝对事由的适用,对于商标授权确权进行了积极主动和较大范围的介入,成为我国商标授权确权的独特现象。绝对事由的准确定位和恰当运用意义重大,其曲解或者误用可能让特定经营者面临“灭顶之灾”。鉴于此,本文拟对注册商标宣告无效程序中绝对事由的法律定位、准确适用和制度重构问题加以探讨,以为其准确适用提供参考。
一、当前以绝对事由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突出问题
总体上看,我国《商标法》在实施中高度重视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考量,在授权确权中,绝对事由的适用越来越频繁,适用范围越来越宽,尤其是近年来,已长期使用的注册商标以绝对事由被宣告无效的现象突出,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绝对事由被扩大适用并变相代行相对事由功能
有些注册商标争议本质上是私权争议,但因保护在先权利的申请宣告无效五年期限已过,商标授权确权机关转而依据绝对事由宣告已长期使用的注册商标无效,在适用法律上有以绝对事由之名行相对事由之实的嫌疑。如在“令狐冲”商标案中,诉争商标(2001年申请,2002年核准注册)由汉字“令狐冲”、拼音“LINGHUCHONG”及图形组成。一审法院认为,“令狐冲”亦系金庸先生创作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的角色名称,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该角色名称已为我国一般公众所熟知,诉争商标申请注册人李时珍公司对此应当知晓,理应避让,其未经避让申请注册诉争商标的行为难谓正当。在案证据可以证明李时珍公司在多个商品或服务类别上注册了670余件商标,包括在多个类别上申请注册了“雅鲁藏布”“珠穆朗玛”“绿野仙踪”等知名地点或景点名称、文学作品名称的商标,已明显超出正常合理的使用范围。一审判决认为李时珍公司申请注册诉争商标具有不当占用公共资源的故意。二审判决认为李时珍公司申请注册上述商标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使用和管理秩序,损害了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了公共资源。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已构成“其他不正当手段”的情形。
值得研究的是:(1)已注册20余年的商标,如果缺乏真实有效的使用,可以通过三年不使用制度予以撤销(以下简称“撤三”);如果已经真实使用,就不再是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注册商标,此时是否还有必要援引其批量注册行为认定其触发注册商标无效的绝对事由?实际使用的商标与其他批量注册的商标在法律定性上应否关联性考量?其他批量注册不使用的商标与争议商标的实际使用可否分开处置?(2)实际使用的商标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实在的标识性财产,对其撤销已不再仅是纯粹的行政管理问题,还涉及如何对待已经实际产生和现实存在的财产权益问题。(3)像“令狐冲”这样的作品元素与他人的在先民事权益以及公共资源、市场秩序等是什么关系?“令狐冲”是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中创作的作品元素,如果需要保护,也是依照民事权益保护,不涉及以占用公共资源之类的绝对事由介入无效宣告。以相对事由保护和宣告无效,涉及超过五年丧失请求权的问题,即落入了《商标法》为稳定秩序而牺牲在先权利的利益平衡的私权秩序范围,不再是保护在先权利意义上的公平问题。在另有“撤三”制度的情况下,如果纯属因超出法定期限无法以相对事由予以救济,再设法牵强附会地纳入绝对事由的调整范围,则必然陷入以公法事由不当干预私法关系、扰乱私权秩序的境地。这种干预虽然直截了当,但打乱了法律既有的制度安排,且具有较强的任意性。这种事例并非以公法事由不适当扩张干预私法关系的偶然现象,而是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值得警惕。这种干预表面上看似符合朴素的公平观念,实则扰乱了公私法应有的平衡和稳定的法律秩序,将导致法律意义更大的不公平。
(二)绝对事由的过多介入损害注册商标秩序
以“其他不正当手段”为由进行的无效宣告已显得过于积极和频繁,动辄宣告使用多年的注册商标无效,必然危及商标权的稳定性和法律预期,实质上是破坏商标注册秩序。如在“BEABA”商标案中,陈某于2013年3月25日申请注册“BEABA”商标(在案件审理中发现陈某名下还存有124件商标),并于2014年8月28日核准注册。核定商品为“医用营养品;婴儿食品;减肥茶;净化剂;人用药;失禁用吸收裤;兽医用药;卫生巾;消毒棉;牙用光洁剂”。爱朵婴童公司为生产销售纸尿裤商品,购买“BEABA”注册商标。在该注册商标转让之前,爱朵婴童公司2014年已获得陈某授权,使用“BEABA”注册商标开设淘宝店销售经营纸尿裤商品。爱朵婴童公司2016年受让该注册商标。2018年,爱朵婴童公司将“BEABA”注册商标转让给杰乔公司。爱朵婴童公司被许可使用和受让“BEABA”注册商标期间,一直研发、生产、销售“BEABA”品牌的纸尿裤等一次性卫生用品。该注册商标转让给杰乔公司后,杰乔公司进一步持续经营使用,通过线上线下投入广告、参展、营销活动等资源培育“BEABA”纸尿裤品牌,具有较高的市场影响力。2019年5月31日,法国某公司申请宣告杰乔公司的“BEABA”注册商标无效。2020年4月2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陈某名下“有124件商标,申请注册在第3类、第5类、第25类、第43类、第44类等二十余个商品和服务上”等事实,依据《商标法》第44条第1款,以“BEABA”注册商标系陈某2014年“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为由,裁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一审法院维持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认为陈某申请注册了包括“肤雅姿”“肤资堂”“妃资堂”“栗上皇”等多件与他人知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并在网站上公开兜售商标,属于“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二审法院认为:“诉争商标虽转让至杰乔实业公司名下,但不能改变诉争商标系‘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事实”“杰乔实业公司主张其对诉争商标具有真实使用意图并进行了多年的宣传和使用,已经建立了较高的市场声誉,形成了稳定的对应关系,但鉴于诉争商标系‘以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取得注册,杰乔实业公司的相关使用行为,无法改变诉争商标注册的非正当性”。
再如,在“麦昆”商标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诉争商标原申请人中某公司在第3类、第5类、第11类、第18类、第25类、第33类、第43类等商品和服务上申请注册了1300余件商标,包括“投名状”“度娘”“晶六福”“欧米嘉琼斯”“肯德西”“盾梵希DONPHANCY”“哲薇娅ZERWIIYR”“宝拉达PORUADAZ”等多个与知名品牌相近似的标志。中某公司作为一家管理咨询服务公司,其申请注册上述商标的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具有攀附他人商誉、声誉以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不具备注册商标应有的正当性,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秩序。群某贸易公司从中某公司受让诉争商标不能改变诉争商标系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非正当性。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41条第1款所指“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应予无效宣告。
在“BEABA”商标案中,受让该注册商标并进行实质性使用的爱朵婴童公司与杰乔公司即使抗辩“具有真实使用意图并进行了多年的宣传和使用,已经建立了较高的市场声誉,形成了稳定的对应关系”,也无法改变该商标申请注册非正当性的“原罪”。即便足以认定争议商标注册人符合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进行注册的情形,但注册之后能否因争议商标的实际使用阻却注册时的恶意,并因基于已经实际产生财产权而不再轻易地予以无效,仍值得思考。该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其他不正当手段”适用效力的绝对性,并且表明其绝对无条件适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再是遏制不以使用为目的申请注册商标的手段,否则不会无视被无效商标已经实际使用的事实。在“麦昆”商标案中,法院也坚持这种观点,未考虑此类商标是否已经实际使用。
(三)既定权利保护不足及对既有秩序缺乏充分尊重
在“传奇贵”商标案中,争议商标“传奇贵”曾于2016年被拉菲罗斯柴尔德集团以多个绝对和相对事由为依据申请宣告无效,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认定其请求不成立,诉争裁定予以维持。在该案中另查明,原告曾申请注册了40件商标,包括在第33类商品上申请注册的“传奇贵”“传奇贵酒”“传奇贵酒庄园CHAUNQIGUIJIU MANOR”“传奇贵酒大师精酿”“传奇贵酒SINCE 1983”等24件含有“传奇贵酒”文字的商标,其中14件商标系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裁定后申请注册的。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裁定后,又在第33类商品上又申请注册了14件商标,属于发生了新的事实,不属于“一事不再理”情形。“其他不正当手段”包括诉争商标申请人采取大批量、规模性“抢注”他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等手段的行为。该案证据表明,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第三人的“贵”商标经过长期大量的宣传使用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很强的显著性,诉争商标与第三人在先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上述商标在文字构成、读音或图形设计、视觉效果上相近似。且除诉争商标外,原告在第33类商品上还申请注册了20余件与第三人在先知名商标相近似的商标,超出了正常的生产经营使用需求,明显具有复制、抄袭他人高知名度商标并借他人市场声誉牟利之目的,其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更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有损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及社会公共利益,故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已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
上述判决在诉争商标已被另案裁定不属于“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而又因原告在该裁定之后又新注册多件相关商标,其批量注册的商标有抄袭、模仿他人知名商标的目的,且没有实际使用意图,连带考量认定诉争商标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不仅有以绝对事由保护他人知名商标之嫌,而且未充分尊重注册商标的稳定性。超过在先权利的五年保护期又在市场上实际使用的商标,已经形成了实际的私人财产权,应当首先尊重其现实存在的财产权,不宜轻易无效。即便此类商标涉及行政程序和行政管理,但行政程序和行政管理毕竟是为商标权服务,必须围绕和服务于商标权,不能主次颠倒。实践中恰恰需要强调的是,公权行使的限定性和强约束性。公权的行使必须以私权为边界,不能随意介入私权范围。动辄以绝对事由无效已长期使用的商标,将冲击产权保护和尊重已经形成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进而动摇商标注册人使用注册商标从事商业活动的预期和信心,不利于营造稳定的营商环境。
上述现象和问题,警醒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商标无效绝对事由的定位和适用标准,确保其适用方向正确,适用效果符合立法目的。
二、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由立法的合分演化及其影响
(一)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由的立法:由混合到区分
2013年修法之前,《商标法》不区分注册商标的无效与撤销,统称为撤销,此后即将无效与撤销区别开来。但就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由涉及的撤销和无效制度而言,其法律条款是一脉相承的。
1982年《商标法》规定了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有争议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撤销的制度(第五章规定的“注册商标争议的裁定”),其中第27条第1款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有争议的,可以自该商标核准注册之日起一年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裁定。”该法未规定撤销的具体事由,1983年和1988年《商标法实施细则》亦未作细化规定。
1993年《商标法》完善了第五章“注册商标争议的裁定”,将“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纳入了可由商标局依职权撤销的范围,且形成撤销程序中绝对事由的法条列举加上“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兜底的规范模式。1993年《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5条将1993年《商标法》第27条第1款规定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行为”界定为:“(1)虚构、隐瞒事实真相或者伪造申请书件及有关文件进行注册的;(2)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复制、模仿、翻译等方式,将他人已为公众熟知的商标进行注册的;(3)未经授权,代理人以其名义将被代理人商标进行注册的;(4)侵犯他人合法的在先权利进行注册的;(5)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5条列举的事项,既包括禁止欺骗商标注册机关的注册,又包括禁止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不正当注册,因而同时包括绝对事由(第1项)和相对事由(第2、3、4项)。1993年《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5条对两种事由的混同规定是当时立法条件下的产物。1993年《商标法》缺乏相对事由条款,但是20世纪90年代“抢注”商标和侵犯在先权利的现象层出不穷,产生了保护在先权利的现实需求。特别是,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之后,我国须履行保护驰名商标、制止代理代表关系中的“抢注”商标等条约义务。在《商标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以《商标法实施细则》解释《商标法》概括性规定的方式,将相对事由纳入进来,如1993年《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5条第2项(保护“已为公众熟知的商标”即后来改称的“驰名商标”)、第3项以及第4项(属于保护在先权利的规定),而第5项至少在形式上成为所有事由的兜底条款。这显然是1993年《商标法》在既定的确权条款框架内,通过《商标法实施细则》作出的变通性规定,所以未区分相对事由与绝对事由。这种权宜之计客观上导致法条适用时亦未区分绝对事由与相对事由,造成注册与撤销程序中绝对事由的不对应和不同一。
2001年《商标法》第41条源于1993年《商标法》第27条和《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5条的规定,但彻底改变了1993年《商标法》第27条第1款规定并由1993年《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5条所解释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内容结构,将绝对事由与相对事由清晰地分开,“其他不正当手段”被作为绝对事由的兜底性规定。2013年《商标法》将以前的注册商标撤销变更为“注册商标的无效宣告”,自此实现了由注册商标撤销到无效的制度转型。虽然这种变化前后是在注册商标撤销和无效的不同商标法语境下界定两种事由,但事由本身的含义是一致的,并未因注册商标撤销转变为注册商标无效,而当然中断了法律适用之间的连续性。
(二)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由的司法澄清
2001年《商标法》引进商标授权确权的司法审查,即此前商标授权确权由商标评审机关终局决定,此后则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转变使《商标法》适用中的许多问题浮现出来。法院和商标授权确权机关对于《商标法》的适用问题进行了诸多讨论,极大地推进了法律适用的全面深入开展。当时一个重要的争论点是如何适用2001年《商标法》第41条规定的两种事由。
2001年《商标法》第41条的清晰规定并未消除实践中对其适用对象的争议。对于“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的首要争论,是其属于2001年《商标法》第五章注册商标撤销(后来的无效)的兜底事由,还是仅为绝对事由的兜底条款。当时商标授权确权机关在解释法律时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认为严格限定“其他不正当手段”的适用范围不利于遏制某些比较多发、危害性较大而又无具体法条规制的行为,如对于有一定影响的而又达不到驰名程度的注册商标的跨类“抢注”、在境外有较高知名度但尚未在中国境内实际使用的域外商标的“抢注”等情形,仍应将其纳入《商标法》第41条第1款的“不正当手段”之中。当时商标授权确权机关仍坚持按1993年《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解释2001年《商标法》第41条的有关规定,认为其第1款关于“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规定仍然包括相对事由的事项,仍然是第41条的兜底条款而不仅仅是其第1款的兜底规定,同时适用于绝对事由与相对事由。如商标评审委员会当时认为,根据《商标法》立法精神和执法实践,“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可以适用于列举性条款以外的其他恶意证据充分的不正当行为,包括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只是在实际操作中应当慎重把握适用条件。当时有的判决同样有扩大适用“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倾向,认为“其他不正当手段”的立法宗旨是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制止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概指“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包括当事人明知他人已使用商标标识的情况下,不仅申请注册他人在先使用的争议商标,还将他人正在使用的其他商标申请注册的行为。如在“无印良品”商标案中,被告的“无印良品”商标在中国境外有注册和实际使用,但在中国境内均没有,原告知道被告的境外商标及其使用情况,在中国境内申请注册诉争“无印良品”商标,被告申请予以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和法院均认为原告在注册和使用争议商标时具有主观恶意,属于“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行为,对其诉争“无印良品”商标予以撤销。在“海豹王SK及图”商标案中,法院认为,石狮统一公司利用其法定代表人在与王佳公司签订代理协议的磋商过程中所知晓的王佳公司上述“王佳SEAL KING”“王佳SK及图”等商标,以自己的名义恶意地申请注册了与王佳公司的上述商标近似的争议商标,违反了《商标法》第15条的规定;同时石狮统一公司的上述申请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了现行《商标法》第41条第1款所禁止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这些判决均未实质性区分两种事由,或者实质上是以绝对事由达到相对事由的目标。
在此期间,法院与商标授权确权机关进行了多次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通过裁判和司法文件,陆续澄清“其他不正当手段”的绝对事由含义,特别是限制以“其他不正当手段”为主要体现的绝对事由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在常州诚联电源制造有限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常州市创联电源有限公司商标撤销行政纠纷案再审驳回通知中,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2001年《商标法》第41条第1款“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作出解释。该案是创联公司以其创意设计和使用在先,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撤销诚联公司在第9类电源开关商品上申请注册的“诚联及图形”商标。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创联公司对争议商标图形使用在先,诚联公司注册争议商标构成《商标法》第41条第1款所指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裁定撤销争议商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创联公司在先使用争议商标图形的证据不足为理由,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商标法》第41条第1款规定的“违反本法第10条、第11条、第12条规定”与“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并列,涉及的是撤销商标注册的绝对事由,这些行为损害的是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利益,或者是妨碍商标注册管理秩序的行为,所以该款规定商标局可以直接依职权撤销商标注册,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而且没有规定时间限制。该条第2款的规定属于涉及商标注册损害特定权利人民事权利的相对撤销事由,为尊重权利人的意志和督促权利人及时维权,采取不告不理原则并规定了五年的时间限制(恶意“抢注”驰名商标的情形其撤销不受时间限制);而且有权提出撤销请求的主体仅限于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涉及在先权利的注册商标争议中,应当适用《商标法》第41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本案应该适用《商标法》第31条及第41条第2款的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及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不当。
鉴于实践中对于“其他不正当手段”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在充分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12号,以下简称《商标授权确权意见》)第19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撤销注册商标的行政案件时,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要考虑其是否属于欺骗手段以外的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对于只是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的情形,则要适用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及商标法的其他相应规定进行审查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2号,以下简称《商标授权确权规定》)第24条沿袭上述规定。司法解释显然只是将“其他不正当手段”作为注册商标宣告无效绝对事由的兜底条款,而不是宣告无效事由的兜底条款。该解释符合法条文义和立法意图。
(三)混合立法的法律适用思路沿用至今
本文之所以回顾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立法合分的演化,是因为旧的法律适用思路迄今仍在大行其道,而分析其立法演化可以看清其存续的原因与问题。具体而言,“其他不正当手段”具有较强的概括力、较高的灵活性和较大的裁量余地,在适用上比较方便。商标授权确权机关对“其他不正当手段”的适用具有路径依赖,《商标审查审理指南2021》对“其他不正当手段”的界定仍涵盖不宜保护的被“抢注”知名商标等,仍以绝对事由为名行相对事由之实,或者实质上变相扩张本不应该存在和保护的在先权利。前文引述的判决亦是如此。这些做法存在的问题,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三、绝对无效事由的制度定位
(一)绝对事由与相对事由的区分依据和法律价值
《商标法》区分宣告无效绝对事由与相对事由的核心是两者调整利益的差异。绝对事由涉及公共政策或者公共利益,属于公法调整的事项;相对事由涉及在先权利,属于私法调整的事项。绝对事由通常关系到公共资源(如《商标法》第11条规定的情形)、公共利益(如《商标法》第10条规定的一些事项)和公共秩序(商标注册秩序);因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触发保护机制的请求人不受利害关系的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商标法》第44条第1款使用的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都可以请求宣告无效;商标授权确权机关可以依职权作为;宣告无效不受时限的限制。但是,《商标法》毕竟是商标权利法,两种事由的设定都是围绕商标权的得失而进行,构成对于商标权的限制。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具有法律保护上的绝对性和优位性,但公法意义上的高强度和严苛性决定了其对民事权利影响较大,因而需要限定绝对事由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特别是,相对事由涉及私权利,2001年《商标法》开始按照“不告不理”的方式在宣告无效程序中给予救济。涉及私权的事项,必须尊重权利人的意愿和调动权利人的维权积极性,请求救济的也只能是“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如2001年修订《商标法》的参与立法者所说:“因为本款(第41条第1款)的违法行为多是民事权益争议的内容,所以本款未赋予商标局直接予以撤销注册商标的权利,而是规定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自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请求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倘若将涉及侵犯私权利的事项变相地纳入绝对事由范围,则有悖私权保护的法律属性,将扰乱私权秩序。
2001年《商标法》在无效宣告中区分涉及私权的事项和不涉及私权的事项,体现了立法意图的深刻变化,使这些规定更加科学合理。无效宣告程序中两种事由的清晰划分和明确规定,更加符合法治要求,可以减少执法的随意性,给当事人更明确的法律预期和更可靠的保障。倘若对于仅仅涉及民事权利冲突的事项,无视《商标法》已经设定的法律界限,随意根据“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予以无效,如仅仅以恶意注册为由,跨类保护有一定知名度的注册商标、保护没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及额外保护显著性强的商标等,而无视有关在先权既定的法律要件,或者超过五年争议期间之后转而采用绝对事由无效注册商标,必然会使《商标法》明文建构的公私法秩序形同虚设,使人们无所适从,从根本上背离法治要求。
(二)绝对事由适用的谦抑性
《商标法》赋予并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其目的是使得权益相关方各得其所,使权利人能够有稳定的权利预期,能够在获得权利之后安心经营,增进社会总福利。因此,维持注册商标的安定和秩序是商标法重要的立法精神和解决争议商标权纠纷的基本原则。例如,对于1982年《商标法》第27条第1款关于注册商标争议申请裁定一年期限的规定,商标局有关专家解读指出,“申请争议裁定的期限定为一年,是兼顾了争议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争议裁定申请人在一年以内可以充分了解到市场情况反映。期限过短,不利于申请人行使申请权;期限过长,又会使被申请人商标专用权长期不稳定。因此,这样规定,有助于督促争议裁定申请人及时行使申请争议裁定的权利,也有利于从法律程序上按期确定新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不可争议性”。此后法律修订使得相关条款的内容更为丰富完善,但这种精神实质没有变化。相对事由涉及的无效宣告期限为五年,其目的也在于平衡权利与秩序。
商标授权确权还可能涉及善意共存、尊重市场格局等。允许善意共存,尊重现有市场格局,是为了稳定市场秩序和保护正当的财产关系。在市场上已经形成稳定的格局,意味着相关商标能够在客观上区分开来,改变此种格局本质上已经不是一个符号、文字等标志要不要存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符号之间的排斥,而是尊重已经形成的财产和产权的问题。
商标无效宣告解决的是诉争商标是否符合注册法定条件,但商标的真正价值源于使用,通过使用建立的市场声誉应当予以保护。实践中,诉争商标可能处于不同的状态,有些尚未投入使用,有些已经大量投入使用。这些情况应当予以考虑并作区别对待。例如,《商标授权确权意见》第1条从诉争商标是否大量投入使用入手,对法院审理案件提出整体性政策导向。对于尚未使用或者未大量投入使用的商标,可依法适当从严掌握授权标准,同时注重保护他人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商号等商业标志权益,尽量划清商业标识之间的界限,防止“搭便车”之类的不正当行为,为品牌经济的发展创设更大的法律空间;对于注册使用时间较长、已建立较高市场声誉和形成自身相关公众群体的商标,法院要尊重相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相关商标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慎重撤销。这种司法政策性描述体现了《商标法》维护安定的精神。特别是,经过大规模商业使用形成稳定市场格局的商标,已以客观实际将诉争商标与他人商标区别开来,没必要以其批量注册或者“傍名牌”等所谓的“原罪”,武断地宣告无效,而漠视市场实际。
两种事由的实质性界限应当分割清楚,绝对事由无论如何不能变相发挥相对事由的功能。《商标法》对于涉及私权利的事项与不涉及私权利的事项进行相对事由与绝对事由的严格区分,是实体正当性的要求。它既涉及如何合理对待和保护在先权利,又涉及商标授权确权机关的职能定位。例如,属于私权利的事项与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无涉,倘若赋予商标局依职权启动撤销的权力,与私权利的属性不符合,将导致商标授权确权机关职能错位;倘若允许没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启动撤销程序,必然妨害利害关系人的处分权,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因此,对于两类情况的区分不能等闲视之。将本应纳入私权保护范围的事项,在不符合该保护要件时又纳入公权调整对象,必然混淆两类情形的法律定位,以及导致法律调整上的失范和无序,损害法律规范的价值取向。关键是,本质上属于相对事由的事项,并不损害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只是因为侵犯在先权利而导致的貌似不公平,达不到需要以绝对事由宣告无效的程度。绝对事由的适用关涉商标注册人和其他相关方的民事权益特别是商标权,对于商标权的剥夺应当保持谨慎和严格的态度,防止恣意。
四、绝对事由的对应性和同一性
(一)我国商标授权确权中绝对事由的非对应性和非同一性
商标注册与无效程序中绝对事由的对应性和同一性是各国商标法的通行做法,两种程序中绝对事由的非对应性和非同一性,以及将“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作为无效注册商标的绝对事由,则是我国的特色。例如,《欧盟商标指令》第二章第二节的标题为“驳回或者无效的事由”(grounds for refusal or invalidity),第4条规定了驳回或无效的绝对事由,包括标识自身的不可商标性及违反公共政策和公认的道德原则等事由,驳回与无效的事由不可能有差异。《欧盟商标指令》不涉及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的问题。《德国商标法》第50条对于违反绝对事由宣告无效的情形穷尽性列举了相关绝对事由条款,没有另外增加事由,且其第8条第2项在绝对事由的列举中有“根据其他法律规定其使用出于公共利益明显地将被禁止的”“提出恶意申请的”事由规定。美国专利法领域有“专利流氓”(patent trolls)、“专利主张主体”(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和“非实施主体”(non-practicing entities)的说法,其中“专利流氓”是指专利非实施主体利用专利进行许可费勒索或者牟取不正当利益。美国版权法领域也有“版权流氓”(copyright trolls)的说法。但是在商标法领域不太会滋生“商标流氓”(trademark trolls),原因是美国商标法比较充分地贯彻商标使用原则,并有相应的保障机制,因而没有额外遏制“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法律需求。美国法上商标授权与无效程序中绝对事由具有同一性。
我国商标实践中存在大量类似“商标流氓”的情形,相当于非以使用为目的而为了利用注册商标牟取不正当利益,实施大量恶意“抢注”及其他不诚信或者貌似不诚信的行为,这类行为经常被定性为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进行商标注册,将其作为重点治理对象而又成为治理依据。因为“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规定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适用的弹性空间较大,且其适用经常被寄予厚望,因而至今据此无效注册商标的适用频率较高,成为以绝对事由撤销或者无效注册商标的核心。但是,《商标法》“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只规定于商标无效程序,未见于商标授权程序,因而前者绝对事由的范围广于后者,因而出现了两种程序中绝对事由的非对应性和非同一性。
在我国《商标法》规定的商标注册条件中,“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并没有对应的规定。从有关方面的解读看,注册商标无效事由针对的是注册不当的商标,当然是注册之时存在不应当注册的情形而给予注册,所以被认为注册不当而应当纠正。如参与2001年《商标法》修订的立法者认为,发生此类注册不当的情况“首先是因为商标注册违反法律规定,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来自商标注册人方面的原因,也有来自商标审查员方面的原因。虽然商标审查有法定的标准和客观的条件,但是在实践中出现错漏、受蒙骗以及审查工作的失误等人为因素,目前还难以避免。尽管如此,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商标注册不当,都应当予以纠正”。商标经过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成为注册商标,但仍不能保证其注册的完全合法性。审查员在对申请商标进行实质性审查很有可能发现不了该商标违反了《商标法》规定的注册条件,但还是给予注册,于是出现不当注册。对此应予撤销;已注册的商标也有通过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对于这种申请期间有欺诈行为的注册商标也应当予以撤销。显然,以绝对事由无效(撤销)注册商标均属于注册之时存在不符合注册条件的情形,其中包括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使得本来不符合注册条件的商标获得了注册,不符合注册条件仍是该类商标的无效(撤销)理由和依据,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只是导致不当注册的原因,而不是不当注册的实体理由。商标局曾经解读认为,“以欺骗或其他不正当手段注册商标,是指申请人采取申报虚假材料的方式,或其他不恰当的方式,致使商标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该商标注册”“利用这些方式注册商标的,其注册本身有瑕疵,不符合《商标法》的规定,故属注册不当”。2013年《商标法》修订的参与者有类似的解读:“商标注册违反法律规定,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为了维护商标注册管理秩序以及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商标当事人的权益,对于违反本法规定,以及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商标,都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按照这些解读,无效注册商标的事由似乎应该都能够与商标授权中的绝对事由对应。
法律适用中,“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被作为《商标法》列举规定的绝对事由以外的兜底性事由,具有无效商标的实体意义,即独立的无效注册商标的绝对事由。这种理解符合《商标法》第44条第1款的文义解释。如在“无印良品”商标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棉某公司申请众多“无印良品”“無印良品”“良品优选”“每日优选”等商标,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攀附他人商誉的恶意情形,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44条第1款所指“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
(二)绝对事由对应和同一的必要性
宣告无效的绝对事由是商标授权之时就存在的足以否定注册商标效力的事由。无效事由可以是授权之后被发现,但必定是授权之时已经存在,将不符合注册条件的标志注册为商标。因此,两种程序中的绝对事由应当是对应和同一的。但是,我国《商标法》因有“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的无效事由,使得无效商标与驳回申请存在事由上的不一致,显然是一种与无效事由的本质属性相违背的特殊状况。
实践中早就提出将“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的事由扩张适用于商标审查程序之中,作为不予注册的事由。如在“the gap及图”商标案中,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字面含义上看,2001年《商标法》第41条第1款针对的是已经注册的商标,但是对于法律的理解,除了领会直接表达的字面含义以外,还应当结合立法精神以及立法目的综合考虑。从该条的立法本意看,其宗旨在于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制止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这一宗旨应当贯穿商标审查、核准、异议和争议程序始终。如果商标局或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商标申请注册阶段即发现该商标申请人系企图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可以适用该条款不予核准该商标获得注册,而不必待该商标申请被核准注册后再适用该条款撤销不当注册商标。其次,《商标法》列举性规定的绝对事由条款是对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和注册的情形作出的规定,而与这些情形并列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行为在《商标法》中并未以列举或者解释的方式给予规定,且在《商标法》的其他条款当中规定的属于以不正当手段进行商标注册的行为也没有全面涵盖所有以不正当手段进行商标注册的情形,因此,2001年《商标法》第41条第1款既作为程序性条款赋予其他单位和个人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的权利,又是一项实体性条款,规定了制止“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原则,故可以在审理商标异议和商标争议案件时适用。按照这种解释,“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规定应当贯穿于商标审查、核准、异议和争议程序的始终。201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北京高院审理指南》)第17.2条规定,“其他不正当手段”的“适用对象既包括已经注册的商标,也包括申请注册的商标”。这意味着“其他不正当手段”可以适用于商标申请程序,说明至今仍是这种扩张性适用态度。撇开这种类推适用是否妥当,现实中之所以需要扩张适用或者类推适用,至少说明两种程序中绝对事由的同一性具有必要性。
当前司法解释和裁判赋予“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无效注册商标的实体内容,或许从根本上不符合立法本意,至少与事物本身的性质相违背,只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而形成,应该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回归立法本意。事实上,当前认定的属于“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的情形大多可以在商标注册条件中找到具体的绝对事由条款依据,或者属于需要通过其他法律路径加以解决的问题,找不到具体条款的情形通常都是不应当宣告无效的情形;即使有在注册条件中不能恰当涵盖的情形,也是罕见的。当前未深入细分,是“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的适用习惯所致。例如,批量注册而不具有使用意图的,现行《商标法》第4条已有规定;批量注册的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的,可以依照“撤三”制度予以撤销,而不必归入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注册。规制注册风景名胜名称等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以及违反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情形,更多是从《商标法》第10条中寻找依据,通过“误导”“不良影响”等概括性条款的灵活解释加以调整。即便仍有通过灵活解释“不良影响”等绝对事由兜底条款不能涵盖、仍需要为维护公共利益宣告无效的罕见情形,也可以考虑通过修订《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的有关内容加以解决,如在“不良影响”的规定之外再加入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之类的兜底规定字样,以使商标授权确权中的绝对事由保持同一,但此种修订的必要性不大,因为“不良影响”等类似的概念已具有较强的概括性。“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不涉及申请注册商标的条件,不宜作为商标审查程序中的绝对事由。
鉴于此,应当尽快否定“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独立实体依据的功能,还实体依据于商标注册条件中的具体条款,因而也就原则上不存在将其适用于商标授权程序中的问题。当前宣告注册商标无效中对于适用“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历史遗存影响、路径依赖和不当适用,更多是习惯造成的,打破这种习惯的关键是认识问题。“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是获得注册商标和导致不当注册的手段,重点是注册的商标不符合绝对事由,如此理解才可以理顺手段与后果的关系,不至于因为手段的不正当而当然导致结果的不正当。即便现实中确有不宜归入商标注册条件的条款而又必须宣告无效的情形,确有保留“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必要性,也应当严格解释,非注册不当的情形最好纳入商标撤销制度之列。当前涉嫌以绝对事由变相行相对事由之实,就是将“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视为独立的无效事由且两者适用边界模糊的结果。因此,必须对“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进行恰当的定位和限定性解释,原则上不能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无效事由。
综上,将“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作为程序性事由而不是实体性的独立无效事由,可以实现商标授权审查程序与无效宣告程序中绝对事由的同一,使无效宣告的注册商标均属于能够在注册条件中有对应的绝对事由的不当注册商标,使其真正地属于不当注册,而不是依据注册之后的事由或者全新的法律政策考量而宣告无效,两者的同一性有利于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安定性和可预见性。
(三)划分授权确权规范与管理规范
授权确权规范与管理规范不能混同。授权确权是解决商标权的获取和灭失问题,主要涉及与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由相关的可注册性问题。管理性规范主要是解决对于不当或者违法行为的管制和处理。例如,“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本身不宜作为无效注册商标的事由,但在确有必要时,可以作为扰乱商标注册秩序予以处罚的事由,如2023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虚构、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材料等不诚信行为给予处罚(第32条);是否由此导致注册商标无效,取决于是否落入相关的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由,这些可注册性事由才是注册商标无效的依据。
五、“欺骗手段”的再定位
与“其他不正当手段”相比,“欺骗手段”的含义相对清晰,其适用范围易于界定,实践中通常没有太大的争议。问题是,“欺骗手段”导致注册商标无效的条件是什么,或者说“欺骗手段”是否足以构成宣告无效的单独事由。
(一)无效宣告中的“欺骗手段”:相对封闭性及非独立和非完整性事由
欺骗手段是商标注册人以在注册条件上虚构事实或者弄虚作假之类的方式,获取商标注册。2016年《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规定,“欺骗手段”是指系争商标注册人在申请注册商标时,采取了向商标行政主管机关虚构或者隐瞒事实真相、提交伪造的申请书件或者其他证明文件,以骗取商标注册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1)伪造申请书件签章的行为;(2)伪造、涂改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的行为,包括使用虚假的身份证、营业执照等身份证明文件,或者涂改身份证、营业执照等身份证明文件上重要登记事项等行为;(3)伪造其他证明文件的行为。《北京高院审理指南》第17.1条规定,“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可以认定属于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1)诉争商标申请人存在使商标行政机关因受到欺骗而陷入错误认知的主观意愿;(2)诉争商标申请人存在以弄虚作假的手段从商标行政机关取得商标注册的行为;(3)商标行政机关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的行政行为系基于诉争商标申请人的行为所产生,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2016年《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中的表述是“欺骗手段”(第2.1条),而2019年《北京高院审理指南》中的表述是“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第17.1条)。《商标法》第44条第1款该种宣告无效理由的规范表达是“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因此,无效宣告的绝对事由仍是商标注册条件中的绝对事由,而“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不是一种独立的无效宣告事由,只是导致不符合绝对事由而获得注册的原因,是否注册不当仍需根据相关绝对事由进行评判,不能仅仅因为有欺骗行为而当然宣告注册商标无效。在商标授权程序中申请人有欺骗行为,因而在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的情况下获得注册,此时欺骗行为与获得注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种欺骗行为属于可以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情形。《商标法》第44条第1款对于“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的规定,显然并非创设一种新的独立无效事由,只是突出了“欺骗手段”这种导致注册商标无效的起因。特别是,无效宣告只是一种处理商标注册不当的法律救济制度,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制裁和惩罚,因而无须将其作为独立的绝对事由。因此,如果对于“欺骗手段”取得注册的行为不再额外设定行政处罚之类的制裁措施,对其进行单独的突出性规定没有实际意义,反而易于引起将其作为独立事由的误解。
(二)“欺骗手段”可否作为驳回申请的事由
《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2条采取了广义的概念,规定:“【商标恶意注册申请】申请人不得恶意申请商标注册,包括:(一)不以使用为目的,大量申请商标注册,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二)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商标注册的;(三)申请注册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有其他重大不良影响的商标的;(四)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故意损害他人合法权利或者权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五)有其他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23年1月公布的《关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加强商标领域诚信建设,明确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商标注册属于商标恶意注册申请,并作为驳回和异议的理由(第二十二条第二项);对虚构、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材料等不诚信行为给予处罚(第三十二条);强化信用监管和信用惩戒(第八十七条)”。
在商标授权程序中发现申请人“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必然会给商标审查带来困扰,也有悖于商标注册申请的诚信原则。为确保商标授权审查的正常秩序,将此作为给予行政处罚的事由,其目的是保障商标授权审查程序的正常进行。这与商标确权中的适用场景和适用目的不同有关。但是,申请程序中能够查明欺骗手段的,还是应根据查明的事实(欺骗的事实)认定其是否符合授权条件,而非以“欺骗手段”为由驳回注册申请。换言之,此种情况下有必要区分授权行为与管理行为。
六、“其他不正当手段”的法律扬弃
(一)“其他不正当手段”规定的由来
自1993年《商标法》引入“其他不正当手段”规定到2001年《商标法》施行之后的相当长期间内,有关方面并未对其含义进行明确的界定。如商标局在释义中认为,“其他不正当手段”是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致使商标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该商标注册”。在此“不恰当的方式”的释义相当于没有界定其内涵。2001年修订《商标法》的立法参与者在对“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的释义中,只解释了“欺骗手段”,未涉及“其他不正当手段”。但是,当时商标授权确权机关对于“其他不正当手段”的适用频率很高,甚至将其作为整个撤销注册商标的兜底性条款。鉴于“其他不正当手段”适用的重要性及其适用中的混乱和争议,最高人民法院有意约束其适用,明确界定其含义。
2010年《商标授权确权意见》起草过程中,“其他不正当手段”的界定是最为关注和最有争议的条款之一,经反复讨论,第19条将其含义界定为“欺骗手段以外的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笔者当时主持该司法文件的具体起草,在起草过程中,基于当时讨论中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和素材,在着重分析和类比《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等禁止作为商标注册、禁止作为商标使用事由体现的立法精神的基础上,对“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含义进行了提炼,即《商标法》规定的禁止作为商标注册、禁止作为商标使用事由主要涉及公共资源、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等问题,这些精神可以为界定“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内涵提供参照。比如,当时尚无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的商标不予注册的明确规定,但批量注册商标而明显不具有实际使用意图的现象比较突出,急于对此寻求对策,而2001年《商标法》第4条第1款商标注册目的的规定暗含了实际使用意图的要求,因而可以从中解读出,无实际使用意图而批量注册商标属于牟取不正当利益,可以归为“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注册商标使用风景名胜区等公共资源名称之类的行为属于“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公共利益则是习惯使用的概括性说法。2010年《商标授权确权意见》第19条就是如此产生的。该界定在《商标授权确权规定》中得到延续,也为2016年《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所采纳。
在“海棠湾”商标案中,李某某在不同类别商品或服务上申请注册了“香水湾”“椰林湾”等与海南地名、景点有关的商标30余件,并且多件商标有转让记录;还曾与海棠湾管理委员会取得联系,希望高价转让“海棠湾”商标。李某某亦未提供其使用“海棠湾”等商标的有关证据。商标评审委员会结合李某某的经营资格、大量申请相关商标等认定其不具有实际使用目的,并会妨碍有正当需求的他人申请商标,认定其扰乱了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情况不足以认定李某某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二审法院认为,上述情况足以认定李某某申请注册争议商标的行为构成“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裁定认为,李某某利用政府部门宣传推广海棠湾休闲度假区及其开发项目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抢先申请注册多个“海棠湾”商标的行为,以及没有合理理由大量注册囤积其他商标的行为,并无真实使用意图,不具备注册商标应有的正当性,属于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情形,属于《商标法》第41条第1款规定的“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在“蘇科版”商标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驳回再审申请裁定中指出,从《商标法》第4条规定的精神来看,民事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应该以满足自己的商标使用需求为目的,有真实的使用意图,其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应具有合理性或正当性。该案盛某某以个人名义申请注册了400余件商标,且涵盖的商品类别极为广泛,显然不是为了正常的商业使用目的。如该案中这种大量注册囤积商标,并无真实使用意图的行为,不具备注册商标应有的正当性,该行为不正当地占用了公共资源,扰乱了商标注册秩序,属于《商标法》第41条第1款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其商标应予撤销。这些裁判将“其他不正当手段”的法律认定重点置于不以使用为目的之上,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商标授权确权意见》“其他不正当手段”规定的原意。
《商标授权确权意见》在界定“其他不正当手段”时特别规定:“对于只是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的情形,则要适用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及商标法的其他相应规定进行审查判断。”这句话在当时有特殊背景,即此前法院和商标授权确权机关对于“其他不正当手段”是否仅适用于绝对事由有争论,这句话旨在明确仅适用于绝对事由,不包括只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的情形,而适用相对事由的情形。当然,不排除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一项申请同时违反公共利益和侵害特定民事权益,此时直接纳入公共利益即可,不再适用是否属于侵犯特定民事权益的相对事由。
(二)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规制非使用性批量注册商标的扩张与扭曲
解决明显无实际使用意图的批量注册商标问题是《商标授权确权意见》制定之前一直受行政、司法和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此将此类多件申请注册商标的情形统称为非使用性批量注册商标。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和业务指导中,先是以个案裁判方式通过解读2001年《商标法》第4条第1款具有要求实际使用意图的立法精神,以此为依据转引第41条第1款“其他不正当手段”,撤销此类无实际使用意图的商标。制定《商标授权确权意见》的讨论中又进一步认为此类行为非为实际使用而旨在牟取不正当利益,因与注册商标的宗旨相悖而可以纳入“扰乱商标注册秩序”之列,进而归入“其他不正当手段”。就当初制度设计的本意而言,批量申请注册商标不是独立的无效事由,是否构成“其他不正当手段”须满足特定要求。如前所述,此前将非使用性批量商标注册纳入“其他不正当手段”的目的是解决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注册问题。当时的背景是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修订《商标法》,对于自然人注册商标一度持放开态度,持有身份证即可以申请注册商标,对其使用意图不作审查,一些意欲通过注册商标发财、开“商标商店”之类的人开始批量注册商标并待价而沽,根本不以使用为目的。后来商标局开始整治,司法部门也在寻求对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应对撤销此类商标的做法应运而生。将批量性商标注册归入“其他不正当手段”的重心是此类商标注册不以使用为目的,不正当地占有和浪费商标资源,背离《商标法》的商标使用精神,而数量较多的批量注册不过是认定不具有实际使用意图的显性特征,即由于《商标法》并不要求实际使用才可以注册,而是留给了注册之后进行使用的缓冲期,即便三年不使用也还有“撤三”制度加以应对,因而在商标审查中据以判断是否实际使用并可以无效商标注册的显性特征不多,将其适用限定于有限的范围,即以批量申请注册为显性标志的非使用性商标,才可以归入应予无效的“其他不正当手段”。
据观察,当前法院和商标授权确权机关对于非使用性批量注册商标归入“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规定和做法,存在过度扩展适用和曲解性界定。例如,《北京高院审理指南》第17.2条特别将“包括诉争商标申请人采取大批量、规模性抢注他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等手段的行为”,规定于“其他不正当手段”,并为此类司法裁判所遵循。2016年《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第2.2.1条对于“申请注册多件商标”“申请注册大量商标”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具体情形进行了细分性界定。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法律适用类型和具体情形,超出了上述司法解释规制此类行为的初衷和预期。
《北京高院审理指南》将“诉争商标申请人采取大批量、规模性抢注他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等手段的行为”作为纳入“其他不正当手段”中的独立无效事由,恰恰忽视了规制的重点是不具有使用意图,即“大批量、规模性抢注他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并不当然具有不正当性,无效此类商标的关键是其以“大批量、规模性”显示出来的非实际使用意图而注册,这是其不正当性的本质所在。而且,如果他人知名商标不属于可以跨类保护的驰名商标,在非类似商品上注册不构成法律禁止的“抢注”,其本身并不具有不正当性,以此限定所禁止的行为没有必要。因此,仅仅是数量多和非侵犯在先权利的“抢注”他人知名商标,并不当然具有不正当性。《北京高院审理指南》在此类行为的规制上舍本逐末。在诸如“燕鸥”商标案之类的裁判中,法院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纠偏性认定,也说明了此类问题所在。
2016年《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归纳的批量注册行为除具有与上述《北京高院审理指南》同样的偏差外,其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三种情形更是偏离了规制非使用性批量注册商标的初衷。具体而言,首先,“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多件商标,且与他人具有较强显著性的商标构成相同或者近似”的情形显然是相对事由调整的范围,且如果在非相同或者非类似商品上注册与他人商标显著性较强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本身不具有不正当性,之所以要纳入“其他不正当手段”,是因为批量注册显示的非使用性意图,《北京高院审理指南》的这种规定以绝对事由的路径干预和扩展了相对事由的界限。其次,“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多件商标,且与他人字号、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及其他机构名称、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等构成相同或者近似的”情形规定的缺陷与上述商标情况相同。2016年《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规定的这两种情形显然是1993年《商标法实施细则》适用“其他不正当手段”旧有观念的延续。再次,“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大量商标,且明显缺乏真实使用意图的”情形接近非使用性批量注册商标的规制本意,但其表达中的“且”字割裂了“申请注册大量商标”与“明显缺乏真实使用意图”的因果性限定关系,即后者是以前者作为显示出来的特征,前者是对后者的界定和限定,而不是两者之间具有并列关系。2016年《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第2.2.2条又进一步规定:“系争商标获准注册后,系争商标申请人既无实际使用行为,也无准备使用行为,仅具有出于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积极向他人兜售商标、胁迫他人与其进行贸易合作,或者向他人索要高额转让费、许可使用费、侵权赔偿金等行为的,可以判定其明显缺乏真实使用意图。”这些判定因素实际上更契合2019年《商标法》第4条第1款非使用性的判定。这恰恰说明“其他不正当手段”可以与《商标法》第4条相对应。
(三)实际使用的商标不能因为“原罪”而被宣告无效
规制“非使用性批量注册商标”的立足点是无实际使用意图,批量注册只是判断实际用途的方式。《北京高院审理指南》和2016年《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将批量性或者规模性商标注册作为单独的“其他不正当手段”的情形,忽视了其非使用性核心,误解了批量注册与非使用性意图的关系,同时用其变相扩张相对事由,使得实践中有扩大适用和不适当适用此类事由的倾向。特别是,将此类行为视为道德谴责的对象,加上将批量性规模性注册本身作为当然不正当行为,使得事后本已实际使用甚至有较高知名度或者几经转让的实际使用商标,因为“原罪”而被无效,在舍本逐末上走得更远。如在前述“令狐冲”商标案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为,虽然李时珍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驰名商标认定批复、湖北省著名商标证书、荣誉证书等证据可以证明“本草纲目”“李时珍”商标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上述证据不足以否定其申请注册诉争商标未构成“其他不正当手段”的无效情形。在前述“BEABA”商标案中,法院同样认为受让之后的实际使用不足以否定构成注册时的“其他不正当手段”。
即便是存在批量注册的情形,但注册之后实际使用或者经转让之后被实际使用,此时即不再属于应当归入“其他不正当手段”的非使用性批量注册商标的范围。首先,从规范目的考量。《商标法》第4条第1款绝对禁止作为商标注册的基点是不以使用为目的,但我国商标注册并不以实际使用为注册要件,在审查核准阶段判断是否以使用为目的,归根结底是一种可能性判断,而在核准注册之后投入实际使用的,实际使用得到了验证,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即不存在,从而不具有适用“不以使用为目的”禁止作为商标注册和无效事由的规范要件事实,因而不应当适用禁止作为商标注册事由宣告无效。其次,避免与保护在先权利的立法精神抵触。实践中确有裁判重点考虑“搭便车”“傍名牌”等因素,即便商标注册之后已实际使用,也据此宣告无效。但是,“不以使用为目的”的禁止作为商标禁止注册事由不在于变相扩张知名商标、显著性强的商标等的保护范围,所谓复制模仿、“搭便车”、囤积牟利等充其量是认定“恶意”和是否有实际使用目的的因素,不是保护的立足点和本体。如果一味以在非类似商品上注册模仿复制他人有知名度或者显著性强的商标,不管是否实际使用均认为应该认定无效,无异于在他人在先商标权利覆盖不到的领域给予变相的扩张保护。这恰恰背离了《商标法》保护在先权利的立法精神,扰乱了商标法构建的私权保护秩序。最后,商标注册数量、“傍名牌”等本身未必是问题。规模性注册本身是用于证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而不是法律调整的基点,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否以使用为目的。正如在“360安钱包”商标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裁定认为,“商标法对于企业申请商标的数量并无禁止性规定,商标法也规定了商标权可以依法流通转让,但商标申请及转让都应该基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商标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商标的使用,发挥商标的真正价值”。“傍名牌”、转售等本身也并非当然有问题,只是在批量申请注册商标的前提下,通常将其作为认定不以使用为目的和具有恶意的因素。如果商标获准注册之后被实际使用,也就不具有“不以使用为目的”禁止作为商标注册事由预设的危害性和违法性,也就无适用该事由的余地。
当然,因事后的实际使用而阻却非使用性恶意注册的构成,司法实践也有较好的探索。例如,《北京高院审理指南》第17.4条规定:“诉争商标申请注册的时间较早,且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诉争商标申请人对该商标具有真实使用意图并实际投入商业使用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认定诉争商标不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在“laduree”商标案中,二审法院指出:“虽然诉争商标的原申请人申请注册了106件商标,不排除其具有商标囤积行为,但是本案诉争商标已经转让给奥商公司,且拉多芮公司未能证明徽商公司与奥商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在诉争商标不违反商标法其他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宣告诉争商标无效,对于合法受让诉争商标的奥商公司将产生不利影响。”在“艾奥比”商标案中,国家知识产权局虽裁定诉争商标予以无效宣告,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虽能初步证明诉争商标投入商业使用,但并不足以证明已经具备较高知名度或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通过使用获得可注册性”。言下之意,受让方如果将商标投入商业使用且“已经具备较高知名度或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使用获得可注册性”消除“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不正当性,避免相应注册商标被宣告无效,即诉争商标经商业使用后是否具备高知名度、美誉度、大规模销售和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等。
综上,无效非以实际使用为目的的注册商标本身并非对此类商标注册行为的惩罚,而是确保注册商标付诸使用。一旦商标实际使用,就可以否定其注册之时的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的非正当性,这是商标法重在促进商标使用的立法精神所要求,本质上也是尊重已经实际产生的财产权。
(四)“其他不正当手段”与“撤三”制度的适用关系
将非使用性批量注册商标纳入“其他不正当手段”是特殊历史条件下解决特定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在适用上具有历史局限性。除2019年《商标法》第4条的完善性规定外,解决类似问题还有“撤三”制度。即便进行了批量性“抢注”,也有三年的期限观察其是否实际使用。“撤三”制度是解决注册商标使用问题的主要渠道。对于商标恶意注册的规制,以批量注册等行为证明商标注册申请人系非使用性目的申请注册而提前主动宣告无效,只适用于事实明显的情形,其他情形应当纳入正面处理商标使用问题的“撤三”制度。
有些裁判已经表明,批量注册与没有使用意图并非直接对应,是否具有实际使用意图有时难以甄别。此时与其认定申请人不具实际使用意图,不如通过“撤三”制度解决,更符合我国商标注册制度的精神。如在“燕鸥”商标案中,第三人中信戴卡公司系诉争商标的权利人,该商标核准注册在第42类工业品外观设计等服务上。原告上海拓臻公司请求宣告诉争商标无效。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诉争商标予以维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中信戴卡公司在多个商品、服务类别上申请注册上千枚商标,已超出其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44条第1款所述“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据此判决撤销无效宣告裁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查明,中信戴卡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铝制件制造及相关研发,系全球最大的汽车底盘铝制件制造企业,占据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市场和国内一半以上的市场,中信戴卡公司目前已注册上千枚商标,诉争商标在核定服务上尚未实际使用,但中信戴卡公司已有使用诉争商标的计划且即将实际使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大规模注册商标行为是否适用2013年《商标法》第44条第1款规定进行规制时,申请注册商标的数量只是一个考察因素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也不是唯一的考察因素,而且客观上也无法设置一个固定数值来判断是否构成大规模注册。事实上,不同行业的企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其对注册商标的需求往往是不同的。大规模注册商标行为如果要被认定为2013年《商标法》第44条第1款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的行为,其注册手段至少应与“欺骗”手段具有同等或者更严重的不当性。单纯的大规模注册行为如果不辅以注册手段的不当性等其他考察因素,往往无法判断其是否属于2013年《商标法》第44条第1款规定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也就无从适用2013年《商标法》第44条第1款规定规制这种注册行为。这些应当考察的因素可以包括是否实际使用或具备实际使用的意图、是否具有明显不当的因素。这里所谓明显不当的因素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情形:无正当理由时针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注册、针对他人已经使用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未注册商标或其他标志的注册、针对他人在其他类别上已经注册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的注册等。中信戴卡公司虽然在多个商品、服务类别上申请注册了上千枚商标,但在案证据不能证明中信戴卡公司申请注册的包括诉争商标在内的商标具有抢注或其他违法申请注册的情形。同时,中信戴卡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底盘制造企业,合法申请并储备一定的商标并无不当。特别是考虑到中信戴卡公司实际从事了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第42类替他人研究和开发新产品、质量控制、车辆性能检测、科学研究、工业品外观设计等服务,具有将诉争商标实际使用于核定服务的主观需求和客观条件。中信戴卡公司申请注册诉争商标并不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44条第1款规定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尽管该案二审判决对于不正当手段的一般性论述引入诸多无关因素,有些提法未必妥当,但其具体分析的思路是实事求是的。
再如,在“极氪”商标案中,“极氪”商标由吉某公司申请注册,指定使用商品为第18类“背包、伞、行李箱”等。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诉争商标注册申请的复审决定认为,吉某公司短期内提交了包含诉争商标在内的大量商标注册申请,且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大量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是出于真实的使用意图,上述行为明显超出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属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违反《商标法》第44条第1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吉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诉争商标由文字“极氪”组成,基于涉案证据该商标标志确为吉某公司所独创,亦具有一定显著特征,但是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所查明的情况,吉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2020年12月24日至2021年3月10日期间,共计申请了900余件商标,被诉决定关于诉争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违反《商标法》第44条第1款规定的认定并无不当。但是,在一审和二审中,吉某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在“行李箱、背包、伞”等商品上已经就诉争商标进行了使用或具有使用意图;结合吉某公司自身企业规模、经营范围、经营发展所需等考量,基于其在行政诉讼阶段所补充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申请注册诉争商标具有实际使用意图,可以推翻被诉决定的认定结论。据此,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和被诉决定,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这些案件表明,商标使用的情况复杂,仅以是否批量注册商标不足以认定有非使用性意图。而且,这些判决也表明,批量注册商标本身不是认定“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决定性因素,是否“抢注”其他知名商标才是重点,因而法院援引“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初衷是变相保护其他知名商标,这与保护在先权利和属于相对事由的相关法律精神相背离。这种适用上左右为难的窘境恰说明该制度的局限性及其适用的不确定性,也说明此类事由可以摒弃。
(五)“其他不正当手段”不宜作为商标无效宣告的绝对事由
如前所述,《商标授权确权意见》及此前的相关裁判将非使用性批量注册商标归入“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原因是当时商标注册条件的绝对事由中缺乏针对性的法条,但此类行为显然又不具有实际使用目的而旨在牟取其他背离注册商标实际使用意图的不正当利益,在缺乏具体条款依据又需实体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情况下,按照通常的法律适用方式只能在当时既定的法律条款之中,通过法律解释的灵活方式寻求依据,所以通过解读2001年《商标法》第4条第1款暗含的商标使用要求及第41条第1款“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兜底条款,以应对此类问题,这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
《商标授权确权规定》第24条对“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规定与《商标授权确权意见》相关内容没有实质差异。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3条曾规定:“商标注册人明显缺乏真实使用意图,大量申请注册与他人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有一定知名度的地名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或者缺乏正当理由申请大量商标,商标评审委员会适用商标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规定不予注册或者宣告无效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但由于尚难以统一意见,且对如“大量”等要件的规定难以量化和确定化,作为司法解释规定条件尚不成熟,最终未能纳入,但允许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适用条件。其实,如果在此种情况下他人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不具有在先权,或者注册有一定知名度的地名商标不违反其他禁止性规定,此类注册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因其不具有使用目的而被纳入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注册之列,重点不是“抢注”而是无实际使用意图。
但是,在当前的法律条件下将适用“其他不正当手段”的情形纳入现有相应的列举性具体绝对事由条款,已具有完全的可能性,因而非使用性批量注册商标归入“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规定和做法已丧失法律基础。2019年修订的《商标法》第4条第1款增加了一项绝对事由,即“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并在第44条纳入无效宣告事由的列举性条款。据此,法律修订已解决上述此前寻求解决的非使用性批量注册商标的宣告无效问题,法院和商标授权确权机关应当转而依照2019年《商标法》的新规定。对于此前发生的行为和案件,应当参照新修订法律规定执行。特别是,虽然《商标授权确权规定》于2019年《商标法》之前施行,其沿用《商标授权确权意见》对于“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规定,应当与2019年《商标法》作相一致的解释和适用。但是2021年《商标审查审理指南》仍按以前的法律适用思路解释2019年《商标法》第44条第1款的“其他不正当手段”,明显不当,应当重新检视。此外,应当发挥“不良影响”等条款的概括调整功能,使其容纳当前适用“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兜底性情形。即使再有必要,最好是在《商标法》第10条第1款修订中引入“违反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不良影响”之类的规定,确保授权与确权的绝对事由的对应性和同一性。
综上,鉴于2019年《商标法》第4条和第44条第1款对于实际使用与商标无效的现有规范进行了针对性完善,此前司法解释和实践对于非使用性批量注册商标纳入“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做法应当纳入2019年《商标法》的相应制度框架之内,无需再单独存在,更不该再进行扩大化和扭曲化地适用。即便对于有待处理的2019年修订法律之前的案件,也应当立足于不抵触确立制度的本意适用,且参照2019年《商标法》相应规定的精神。
结 语
我国《商标法》以具体法条列举加上“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兜底的方式,确定了注册商标无效宣告事由的立法模式,致使无效宣告与注册申请的绝对事由不具对应性和同一性。“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纳入无效宣告事由是我国商标立法的独创,且在商标确权中经常被频繁适用,出现疑似以绝对事由变相代行相对事由功能、轻率宣告已长期使用的注册商标无效等问题,引发了对维护既有商标权利、稳定商标注册预期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担忧。我国早期商标立法未区分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由,加之法律解释的路径依赖,导致商标授权确权实践中仍受两种事由混同适用的观念影响,造成两种事由适用上的诸多偏差。特别是,绝对事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立法产物,曾被赋予特定的历史含义和功能,但其使命已经达成,当前已无存在的必要,商标立法应当回归商标授权与无效宣告的绝对事由的对应性和同一性,“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不宜作为宣告商标无效的绝对事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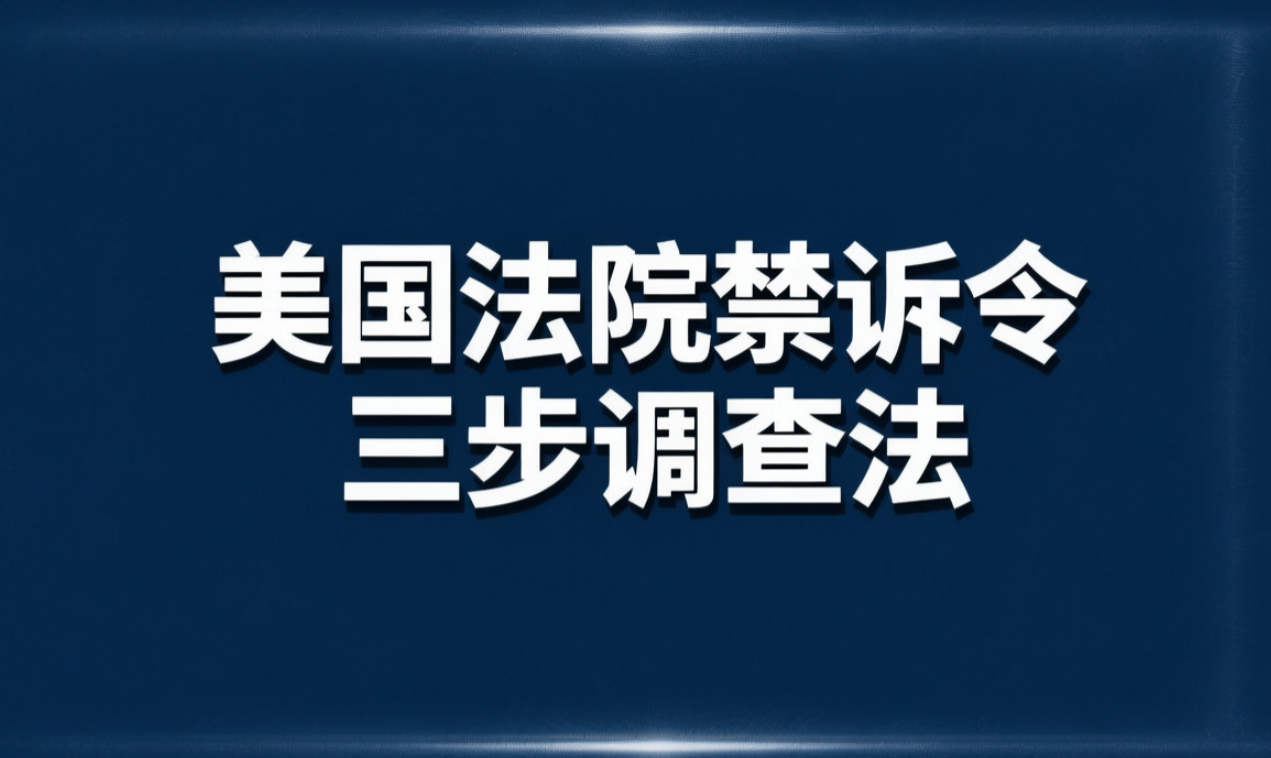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上一篇
上一篇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