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专利
专利 -
 商标
商标 -
 版权
版权 -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
 反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 -
 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 -
 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
 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 -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律师动态
更多 >>知产速递
更多 >>审判动态
更多 >>案例聚焦
更多 >>法官视点
更多 >>裁判文书
更多 >>摘要
数字经济催生出新的音乐作品创作样态,音乐表达的混音创作成为数字环境下的一种潮流。然而,混音创作的日渐流行与我国版权许可制度的疲于应付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有效治理混音创作、促进混音市场的有序化发展,学界对此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总体而言,美国合理使用“四要素”的判断标准在目前著作权体系下仍存有局限性、知识共享协议效力未定,无法满足混音作品创作实际需求以及法定许可制度对混音创作存在的负激励作用难以妥善处理好混音创作授权的现实困境,有必要借助民法领域的默示行为理论构建混音作品的选择退出默示许可制度,使得作品权利的授予以默示的方式作出,降低版权交易许可成本,推动混音创作市场繁荣发展。
关键词
混音创作;合理使用;知识共享协议;法定许可;选择退出;默示许可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音乐作品的混音[1]创作受到音乐制作者的广泛青睐。混音作品的创作需要从在先音乐作品中撷取部分声音片段用以再次合成[2],因其以在先作品为创作“原材料”,便难以避免对在先作品可能存在的侵权行为。譬如,美国纽约南部地区法院在审理第一个涉混音创作纠纷时,便指出即使是最为微量的音乐采样也必须获得权利人的许可。[3]考察我国目前混音作品创作市场的发展现状,虽然国内对此涉及的案件纠纷较少,但需要警惕的是,混音创作行为仍游离于版权的灰色地带,依旧面临着版权侵权的风险。随着Web2.0时代的全面到来,版权创作市场以及版权文化将得到进一步的激励和推进,版权创作主体之间的固有关系将会受到技术冲击并发生改变,美国版权法学者Samantha Von Hoene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传统版权创作的“只读文化” 将会转型为“作者与消费者融合”的“读写文化”[4]。诚如所言,Samantha Von Hoene教授意识到新技术创作方式下,音乐创作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性“读写文化”的转变,但同时也要注意的是,在混音创作的版权市场中,如何处理好在先作品权利人与混音创作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化解混音创作的版权风险,促进混音产业的有序发展。
二、混音作品创作著作权法治理的现实困境
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目的旨在合法限制著作权人的权利,防止因为著作权人对知识产权的过度垄断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妨碍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如果混音创作行为能够满足新《著作权法》第24条项下的12种情形(由于法律、行政法规并未对此规定其他情形,此处可以暂不考虑法律、行政法规的特别规定),则可以依法认定混音作品创作对于其他音乐作品的编制和录用行为是合理使用,即混音作品创作者可以在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的前提下,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便可以使用其在先的音乐作品,当然这种利用行为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然而,从我国《著作权法》第24条项下的法定抗辩权利虽然可以被混音创作者所援用,但抗辩结果却往往并不乐观。有研究指出,总体上看,重混音乐创作人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很难满足合理使用的要求[5]。
从著作权法为知识信息传播的制度设计来看,作品的传播途径主要可以分为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以及权利授权许可三种方式。混音作品的创作在目前的版权体系中不宜认定为合理使用,由此混音作品的传播方式仅剩法定许可和权利授权许可使用两种路径。一方面,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并未对混音创作设定法定许可,在现行版权法体系之下,混音创作者只能通过权利授权许可使用制度才能进行音乐创作。另一方面,混音作品的产生并非像传统音乐制作般只要取得单个音乐作品词曲作者或者录音制作者的许可便可以进行剪辑和摘录,相反除此之外,混音创作需要对大量的音乐作品片段进行重组,继而产生出新的音乐作品。这便意味着混音创作者需要主动寻求每一个音乐作品的权利人进行协商谈判以获取作品的授权许可。由此,导致的问题便是混音创作所带来的成本将陡然攀升,进而阻碍混音作品产业的繁荣与发展。[6]
三、混音作品创作行为的纠纷解决路径及评述
为了缓解混音创作人与原音乐作品权利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突破混音创作面临的版权困境,业内专家学者纷纷对此提出不同的解决路径,考察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有以下3种主流方案:其一,改进我国的合理使用制度,通过对合理使用制度的扩张将混音创作行为纳入合理使用的范畴[7]。其二,推广知识共享协议,平衡混音创作者和原音乐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8]。其三,为混音作品创作设立“法定许可”[9]。以下分别对于这三种规制混音创作行为的解决方案进行评价。
(一)“四要素判断法”在当前著作权法语境下的局限性
1976年《美国版权法》对作品合理使用的判定采取开放式的“四要素判断法”,根据美国《版权法》第107条之规定内容,合理使用的判定标准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该使用的目的与特性,包括该使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或是否为了非营利的教学目的;二是该版权作品的性质;三是所使用的部分的质与量与版权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四是该使用对版权作品之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有观点认为,美国版权法“四要素判断法”允许裁判者根据四个要素综合判断混音创作使用作品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行为,具有高度的灵活性[11]。譬如以作品使用目的来看,一方面,混音创作者的截取和重组既有作品片段的利用行为,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对既有作品进行“批判、评论或者说明”,因此,截取和重组的创作行为不宜认定为转换性使用[12]。另一方面,从混音创作者的主体来看,职业混音创作者一般是出于营利的商业目的进行,而业余创作者则是为了满足自我娱乐性的需求。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版权法合理使用的“四要素”判断法既有灵活性,但在当前著作权法语境下亦有局限性,不能简单移植域外的立法经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对作品的合理使用行为确立了“三步检验法”的判断标准,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允许复制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与该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利益。”[13]我国作为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在新《著作权法》修改之际明确纳入了“三步检验法”[14]的判断标准,我国新《著作权法》在承继“三步检验法”的封闭式立法基础上进一步限制法院在个案中创设新的权利限制。王迁教授进一步指出,该制度规定的作用都不在于允许法院在《著作权法》明文规定的各项权利限制之外,在个案中自行认定一种未经许可利用作品的行为不侵权[15]。换言之,就混音创作的行为认定而言,法院在处理混音作品中利用他人作品的行为认定时不能试图为混音创作找寻不侵权的理由而再自行创设新的权利限制。从这个层面来看,尽管美国《版权法》合理使用的四要素判定标准在个案认定中具有高度灵活性,但法院也不能在混音作品侵权纠纷案件中直接适用该规则对音乐作品的权利人的合法权利进行新的权利限制。概言之,在现行版权法体系下不宜通过“四要素判断法”对混音创作行为的解释来为原音乐权利人创设一个新的权利限制,这将会违背我国立法所确立的“三步检验法”的判断标准。
(二)知识共享协议效力未定,与热门音乐作品许可脱节
美国版权法学者Kerri Eble教授指出,在传统“保留部分权利”的版权交易规则下,知识共享协议能够减少或消除个人许可的负累,大幅度降低音乐版权行业的许可谈判成本[16]。
尽管如Kerri Eble教授所言,知识共享协议具有降低音乐版权行业许可交易成本的优越性,但现实情况是,该协议在我国音乐版权领域的普及化程度并不高,很少为混音创作的主体所采用。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知识共享协议在我国版权法许可制度中的效力未定。目前,无论是立法还是诉讼层面,我国均没有明确承认知识共享协议作为一种著作权许可协议的法律效力[17]。知识共享协议的效力问题是阻碍音乐作品权利人参与知识共享活动的主要因素,混音创作者试图通过既有的知识共享协议以较低成本的方式实现高效授权和消除侵权顾虑的目的,然而知识共享协议本身的效力问题将从根本上影响混音创作者参与目的的实现。其二,知识共享协议与热门音乐版权授权许可脱节。热门音乐始终是混音创作的重要材料来源,混音创作所要寻求版权许可的对象也主要集中于热门音乐的版权人。然而,知识共享协议的无偿许可和不可撤销性的特征对于热门音乐作品的版权人吸引力不足,相反热门音乐版权人更愿意采取独占许可抑或是排他许可来取得更为丰富的市场效益。概言之,知识共享协议在当前的著作权法许可模式下效力未定,与热门音乐版权授权许可脱节难以起到优化混音创作授权许可的作用。混音创作者与原音乐权人采取知识共享协议的许可方式,难以有效形成稳定的授权许可关系,不利于混音创作行为效力的安定性。
(三)法定许可制度对混音创作的负激励作用
美国版权法学者Peter Menell教授认为可以尝试为混音创作设立“法定许可”,我国国内同样也有学者持该观点,并认为依赖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可以在数字音乐中准确标示追踪参与音乐创作的各方主体实现新作品收益按照“取样比例”的分配方式[18]。但是,当我们过分追求采取法定许可降低混音创作的交易成本时,却时常忽略了制度的实现方式对混音创作可能产生的负激励作用。
首先,法定许可的设置理由主要包括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降低某些使用人的义务成本以及降低某些行业的垄断程度[19]。可以说,法定许可制度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公共属性的色彩。例如我国新《著作权法》第35条[20]对报刊转载的法定许可,其设置目的便在于满足社会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同时避免某一报刊对于信息的垄断。尽管法定许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混音创作的许可成本,简化混音创作的许可程序,但是在本质上混音创作的授权许可行为依旧是只关乎混音创作者与原音乐权利人之间的私主体的利益关系,著作权法不应将私主体的利害关系上升到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整轨道上来。
其次,为混音作品创作设立“法定许可”将会导致法定许可适用范围在著作权法体系下的不当扩张。混音作品创作涉及的在先音乐录音制品数量庞大,如果将混音创作者利用他人录音制品的行为纳入法定许可将会迅速扩张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在当前新《著作权法》实施的背景下,倘若为混音作品创作设立新的“法定许可”内容将会对著作权法的秩序稳定性造成影响,损害著作权法的法律权威。
最后,法定许可通过弱化知识产权的排他性来达到提高作品交易效率的目的,但同样也会损害原音乐作品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法定许可对财产权排他性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定价权的转移;二是许可权的转移[21]。一方面,混音创作“法定许可”制度下定价权的转移实质上剥夺了混音创作者与原作品音乐权利人协商谈判的机会,由法律直接干预定价的混音授权“法定许可”难以反映混音作品产业供求关系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原音乐作品权利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混音创作“法定许可”制度下许可权的转移虽然可以简化混音创作的许可程序,但同时也过分增加了权利人的负担。法定许可给予了所有混音创作者未经原音乐权利人许可便可以使用该作品的“便捷通道”,但是,原音乐权利人在面对数量庞杂的混音创作者更是难以追踪和及时了解自己音乐作品的真实使用情况,将会直接影响到音乐作品权利人许可费的收取问题。
四、混音作品创作困境之化解:“选择退出”默示许可制度的出场
(一)从“财产规则”走向“责任规则”的选择退出默示许可制度
传统版权法下的权利授权许可方式是一种“选择进入”协议模式,即在作品完成后,版权人依靠法定专有权利控制作品的初始权利状态,只有事先取得版权人许可的情况下,作品才正式进入流通环节[22]。在“选择进入”的普通许可之中,权利人受到 “财产规则”的保护,即混音作品的创作者使用音乐作品必须取得原音乐作品权利人的许可,否则构成侵权[23]。换言之,在“选择进入”模式下,混搭作品的创作者需要主动寻求版权人的许可来换取作品进入流通环节的机会,也即寻求版权许可授权的义务在于混音作品的创作者。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当面临海量的作品授权需求,混音作品的创作者在传统授权许可方式下需要承担高昂的交易成本。
但以“责任规则”为基础的选择退出默示许可制度,允许作品使用者在著作权人未作出“不得使用作品”的声明时,可先使用作品后付费[24]。在从“财产规则”走向“责任规则”的选择退出默示许可制度将混音创作授权程序所产生的一部分义务责任间接转移到了音乐作品权利人身上,在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配置上进行利益平衡。在制度的实现效果层面,从混搭作品的创作者角度来看,混搭作品的创作者在版权授权许可程序中的义务发生转变,从原先的寻求音乐权利人授权许可的义务转变为注意音乐权利人发布权利声明的义务。对于前后两种义务的违反都将导致混音创作行为被认定为系一种侵权行为。从原音乐作品版权人角度来看,在音乐作品完成后,其作品的权利状态推定进入流通环节,原音乐作品版权人可以通过对外公布“不得使用”的权利声明来控制其音乐作品退出音乐市场。
可以预见的是,融媒体时代,海量作品的权利授权正在不断挑战传统版权体系下的“一对一”的授权模式,更新版权授权方式成为应对媒体融合时代知识产权信息创造与传播的必然举措。而“选择退出”默示许可制度能最大化降低版权许可交易成本,促成音乐混搭作品的创作者与原音乐版权许可人合作,实现双方在混音创作领域的利益平衡。
(二)“选择退出”默示许可制度功能的实现
混音作品“选择退出”默示许可制度的顺畅运行仍然需要从保障相关主体的知情权、原音乐作品权利人获酬权的实现以及音乐权利人自由退出三个方面进行有效衔接,实现原音乐作品权利人和混搭作品创作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避免出现过分剥夺原音乐作品权利人的利益来促进混音市场的发展。
首先,保障参与主体的知情权。原音乐作品权利人在“选择退出”的默示许可模式下推定其音乐作品进入音乐市场,但这并非表明该许可模式剥夺了音乐版权人的一切权利,音乐作品权利人对其作品使用情况的知情权是默示许可制度的重要环节,因为音乐作品创作者当然享有基于智慧创造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保障原音乐作品权利人获酬权的预期利益,关键在于满足权利人知情权的顺利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连接上下游产业主体的桥梁,具有兼顾权利保护价值和利益平衡价值的应然多元功能[25]。在混音作品产业的信息传递与交流中,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保障原音乐作品权利人对其作品在音乐市场使用情况的了解和知情过程中应当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其次,保证原音乐作品权利人获酬权的实现。混音作品“选择退出”的默示许可制度设计将权利人的音乐作品事先放置到流通环节导致版权许可的定价权出现转移,而规范性、有序性的许可费定价将成为原音乐作品权利人获酬权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版权立法尚未对此作出类似法定许可使用费的有关内容,又因法定许可在定价效率方面存在的局限性,难以反映混音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变动,不妨鼓励混音作品产业的相关市场主体进行集体协商定价,并根据市场具体状况进行适时调整。
最后,保证原音乐作品权利人自由退出的权利。混音作品选择退出的默示许可机制改变了原音乐作品权利人在授权许可环节的主动性地位,增加了原音乐作品权利人的被动性义务。在原音乐作品权利人的被动性义务提前设定的规则下,必须保证原音乐作品权利人自由退出市场的权利。否则,混音作品选择退出的默示许可机制的制度设计便会沦为侵害音乐作品权利人的工具,而丧失正当性基础。保证原音乐作品权利人自由退出市场的权利,其意义一方面是对版权私权利属性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维护混音作品产业有序化发展的考虑。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混音,又被称为“音乐取样、音乐混搭、混编”等,英文表述为music remixing,music sampling等。
[2] Bryan A.Garner,Black’s Law Dictionary,Thomson West Press,2009,p1458.
[3] See Grand Upright Music, Ltd. v. Warner Bros. Records, 780 F. Supp. 182, 183(S.D.N.Y. 1991).
[4] See Samantha Von Hoene, Fair Use in the Classroom; A Conundrum for Digital User-Generated Content in the Remix Culture, 7 Hastings Sci. & TECH. L.J. 97 (2015).
[5] 袁旺然:《重混音乐创作中利用他人作品行为的法律规制》,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49页。
[6] 有研究表明,一个音乐作品的商业性使用,平均需签订二十个以上合同。参见宋健:《涉音集协卡拉OK音乐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件使用者利益的特殊考量》,载微信公众平台2021年3月10日,https://mp.weixin.qq.com/s/aUPM9OpcVsEAP4Nf_CM5NQ.
[7] 胡开忠:《论重混创作行为的法律规制》,载《法学》2014年第12期,第89页。
[8] 易玲,邢家仪:《重混创作行为的著作权法规制研究》,载《湖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133页。
[9] See Peter Menell.A Remix Compulsory Licensing Regime for Music Mashup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Copyright and Creativity in the 21st Century(2020).
[10] 十二国著作权法翻译组:《十二国著作权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1页。
[11] 黄云平:《论混编创作行为的实质与规制》,载《浙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209页。
[12] Leval 法官在 1990 年首创“转换性使用”概念,将其定义为“以原作品为原料,增添新信息、新美学和新见解”。1994 年,David Souter 法官在 Campbell 案中对转换性使用的定义进行了完善:“转换性作品以进一步的目的或者不同的特征增添了新的内容,使用了新的表达、意义或信息”。See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 510 U.S. 569, 591 (1994).
[13] 参见《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第9条第(2)款。
[14] 参见《著作权法》第24条第1款。
[15] 王迁:《<著作权法>修改:关键条款的解读与分析(上)》,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1期。第29页。
[16] See Kerri Eble, This Is a Remix: Remixing Music Copyright to Better Protect Mashup Artists, 2013 U. ILL. L. REV. 661 (2013).
[17] 朱钰涛,黄武双:《网络背景下知识共享协议在我国的适用》,载《人民司法》2020年第7期,第94页。
[18] 宋海燕:《数字音乐取样混音作品的版权困境与未来》,载《中国版权》2021年第2期,第19页。
[19]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第35条第2款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21] 熊琦:《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解构与制度替代》,载《知识产权》2011年第6期,第39页。
[22] 郭威:《版权默示许可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23] 王国柱:《著作权“选择退出”默示许可的制度解析与立法构造》,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第107-108页。
[24] 刘友华,魏远山:《知识付费平台的著作权纠纷及其解决》,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6期,第77页。
[25] 李陶:《我国网络音乐独家许可的运行逻辑与完善策略》,载《法学》2021年第6期,第10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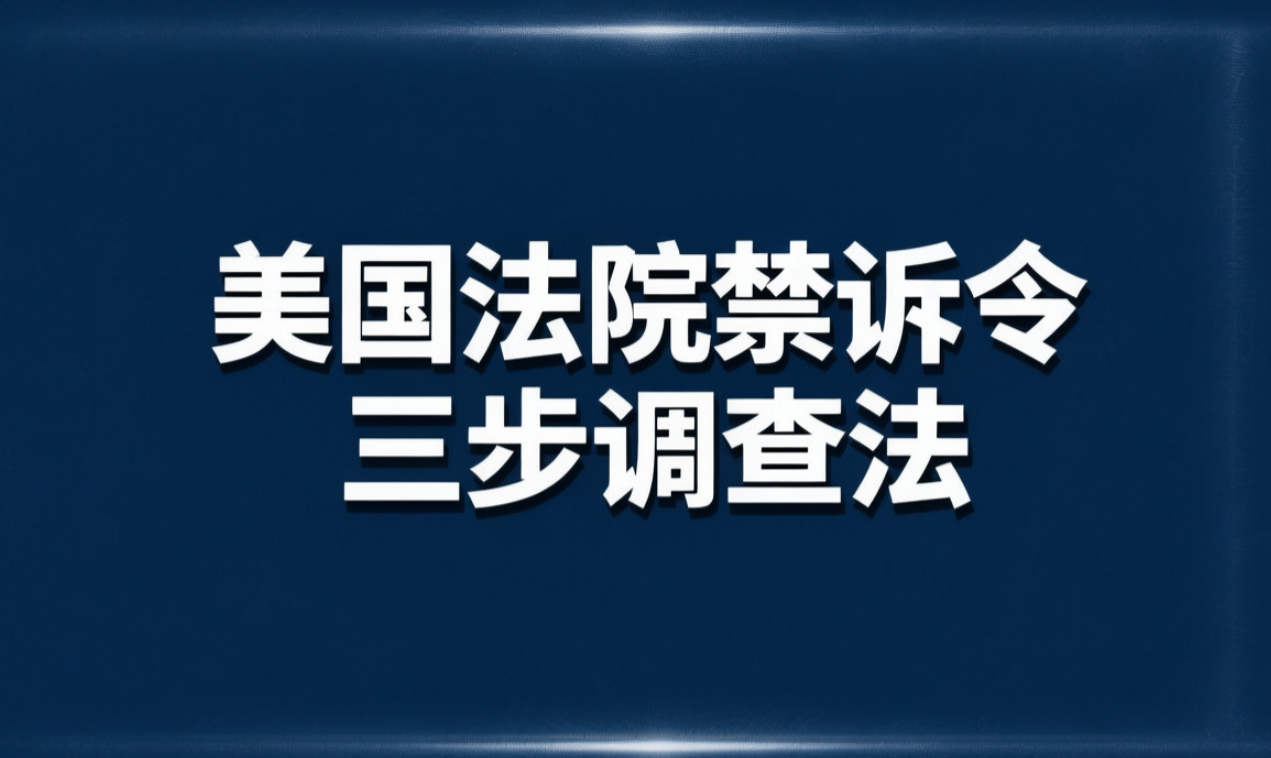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上一篇
上一篇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