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专利
专利 -
 商标
商标 -
 版权
版权 -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
 反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 -
 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 -
 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
 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 -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律师动态
更多 >>知产速递
更多 >>审判动态
更多 >>案例聚焦
更多 >>法官视点
更多 >>裁判文书
更多 >>作者 | 衣庆云 东北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著作权法》自从启动第三次修改至今,已历近十年的漫长过程,其间公开的草案即有四、五稿之多,而这几稿草案中关于视听作品定义和权利归属的条款每稿都不一样,足见立法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纠结程度。日前公开征求意见的草案二审稿较之此前的草案有了较大调整,但再次受到质疑。那么,围绕视听作品著作权立法的争议的症结到底在哪儿,如何破解呢?本文试析一二,唐突之处还请同行指正。
立法者究竟在纠结什么
纵观几稿草案,以“视听作品”的概念取代现行法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改变现行法涵盖范围不足的弊端的认知是一致的,在条款历次修改中得到一致的贯彻,但关于权利归属的条款则变动较大。在立法机关审议之前,草案主要是在视听作品的原始著作权规定直接归属制片者还是增加一个首先尊重与作者之间的约定这两个选项之间摇摆,但到审议一审稿时,就确定了仍然维持现行法的直接归属制片者的立场。然而,二审稿在延续这一权利归属立场的同时,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调整,具体是将作品名称由“视听作品”改为“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及其他视听作品”,在此基础上,将权利归属进行了分类处理,电影作品和电视剧作品的原始著作权继续规定属于制片者,不属于电影作品和电视剧作品的其他视听作品(以下简称“其他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再区分两种情形处理:属于职务作品或合作作品的其他视听作品和不属于职务作品或合作作品的其他视听作品。
有学者认为二审稿的上述规则设计过于复杂且不必要,原规则自1991年《著作权法》实施以来,在现实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实无如此大动干戈进行调整的必要。然而,似乎很少有人体察到立法者在这一问题上纠结的原因。依现行法,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原始著作权归属制片者,但对这个“制片者”的主体所指一直未给出解释,教科书通常解释为“投资者”,司法上一般将电影或电视剧署名的“出品”或“摄制”等推定为制片者(比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10.4条的规定)。而在以“视听作品”的概念将此类客体的范围扩大后,对于大多数其他视听作品而言,创作主体和创作方式与电影、电视剧以外的其他作品并无实质不同,著作权根据情况分别归属自然人作者、法人作者或者适用合作作品、职务作品的规则即可,制片者更像是个无关概念。于是,在一审稿时,就以“制作者”的概念替代“制片者”,试图达到在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和其他视听作品中可以通用的目的。而或许考虑到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与其他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应有所区别,二审稿又恢复了前者原始著作权人制片者的称谓,而对后者的著作权归属适用合作作品或职务作品的规定。
因此,二审稿将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规则体系设计的比较复杂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简单点说就是因为其他视听作品的相关主体中可能实际不存在一个“制片者”。以前作品限定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时,并无这个问题;现在此类作品范围扩大到其他视听作品时,问题就出现了。
如此看来,问题既然因“制片者”而起,解决问题的思路就还应该从这个概念着手;首要的问题是,这个制片者到底是谁,我国著作权法是如何引入这个概念的。
谁是“制片者”
为了理解这个“制片者”,我们可以通过音乐作品和录音制品之间的关系进行类比。我们知道,在没有录音技术之前,就有音乐作品,音乐作品可以脱离录音制品而表现,二者的关系很容易理解。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理念中,正如音乐作品和音乐作品的录制品之间的关系一样,电影作品与电影作品的录制品同样是被区别开来的,所谓电影作品的客体被明确定义为电影作品本身而不是其录制品,电影录制品之上单设一项邻接权由制片者享有(德国著作权法第94条)。这样,电影作品的编剧、导演等就是电影作品的“作者”,而电影作品的录制者就是“制片者”。英美法系则不这样认识电影作品,英国版权法就规定,电影作品就是指“能够通过任何手段再现运动图像的任何媒介上的录制品”(英国版权法第5B条)。在著作权归属上,大陆法系的模式简单说就是首先坚持一切作品的原始著作权归属作者的基本立场,但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推定由制片者自始享有排他使用权;而英美法系则不必如此拐弯抹角,既然电影作品就是指那个录制品,著作权自然就原始归属录制品的制作者——制片者。
那么,中国著作权法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呢?我们是“融合”了两大法系:一方面像大陆法系那样区分了作者和制片者,另一方面又像英美法系那样规定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原始归属制片者。这就是我们在电影作品归属问题上始终游移不定、左支右拙的根源了。
顺应技术发展的选择
随着技术的进步,围绕电影作品有两个方面的关键变化:一是电影作品不再必须以胶片为载体、以拷贝为发行方式了,数字电影成为主流;二是视听作品的范围急剧扩大,不属于传统电影和电视剧的视听作品逐渐成为著作权法不能忽视的调整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制片者”的身影已经越来越模糊。著作权法应该顺应技术的发展,不再拘泥于作者和制片者的划分,制片者即作者。英美法系的模式简便直接,经年实践无碍,可以借鉴。且我国著作权法近三十年一直沿用制片者原始取得著作权的模式,实质上就已经是英美法的模式了,何必还一直附加一个大陆法系的“尾巴”而受到羁绊呢?在具体规则设计上,既然制片者和作者身份归一,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实际上已不必专门特殊规定,法人作品、合作作品、委托作品等的既有规则体系即满足调整的需要,尤其是有了法人可以视为作者的规范,就不存在什么障碍了。如果感觉这一方案稍嫌激进,可以设计一个明确视听作品作者的条款以为过渡。有人可能担心现行法框架下的那些“作者”的权利问题,但实际上,现行法关于作者“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的规定,“作者”们的权利源于合同,直白一点说,本来就没有作者的地位。这一问题在英美法系模式下可以处理,我们照样可以处理。因此,改造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的两“者”关系,即可破解目前立法选择上的僵局,且能化解技术进步给传统著作权法体系带来的挑战。
录像和录像制品
实际上,从著作权法本轮修法最初的草案到现在的二审稿,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对于不构成作品的录像或视听非作品如何处理的问题。前期的草案在邻接权章节取消了录像制品的表述,试图用视听作品涵盖所有以活动影像表现的客体,实际上是将不构成作品的录像排除著作权法的调整范围。
一审稿和二审稿恢复了现行法“录音录像制品”的概念表述,表面上看问题得到了解决,即:构成作品的活动影像统称视听作品,享有狭义著作权;不构成作品的活动影像就是录像制品,享有邻接权。然而,邻接权是指作品传播者的权利,对既有基础作品的录制(典型如将电影或戏剧制成光碟传播),才是纯粹意义的录像制品。而对于那种对客观景物、人的行为、社会活动等的录制成果,称之为录像制品名不副实,也不属于邻接权的客体。这类客体中的部分,尤其是经过后期制作的(体育赛事转播画面即属此类)客体,可能达到作品独创性要求,当然可以被视听作品涵盖;但问题是那些达不到作品独创性要求的客体,既不能通过著作权保护,也不能通过邻接权保护,但附着于其上的民事权益法律完全不保护又不合适。可能有人说,何必那么教条,就以录像制品的概念统摄这类客体不就行了嘛。这的确是一个变通性的方案,但这需要在立法上,至少是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才能给因此类客体引发的争议提供法律依据。但笔者更倾向的方案,是坚持概念的规范性、准确性,将录像或视听非作品与录像制品区别处理,前者也享有“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德国著作权法第95条就是这样处理的,录像或视听非作品被称为“活动图像”,以区别于电影作品),这样,还可以将达不到作品独创性要求的照片、影视剧截图等一并归为此类客体,终止此前实务中受到诟病的摄影作品独创性认定标准偏低的局面以及真正解决影视剧截图等客体定性的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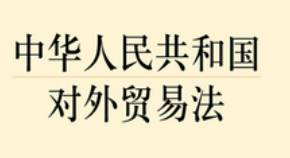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上一篇
上一篇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