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专利
专利 -
 商标
商标 -
 版权
版权 -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 -
 反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 -
 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 -
 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
 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 -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律师动态
更多 >>知产速递
更多 >>审判动态
更多 >>案例聚焦
更多 >>法官视点
更多 >>裁判文书
更多 >>
“非遗”确定传承人相当不易
“要准确认定一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难度很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很多‘非遗’项目都来自民间,同一个项目的‘艺人’技艺水平参差不齐,并且其传承情况往往也很混乱”。
“非遗”技艺最早时多沿用家族传承的方式,但仍不可避免技艺的流散。一方面,家族子嗣中的传承者并非一人,世代传承的结果必然将形成规模庞大的“树状”列表。另一方面,这些传承人难免会因为各自原因不能久居一地,而其自身所传承的技艺也就一并“流走”他乡,很有可能出现技艺的“入乡随俗”。这种技艺的融合、发展和演变给后世对传承项目的脉络梳理添加了不小的麻烦。更为困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民间传统工艺、技术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家族传承模式,而融入了师徒传承的方式。这使“非遗”项目大部分都呈现了复杂的、模糊不清的网状传承脉络。
据这位负责人讲,河北省在吴桥杂技这个项目传承人认定上就花费了很大力气。在吴桥县国办、民办的杂技学校星罗棋布、学员众多,杂技艺人遍布五湖四海,有的长年在国外演出,他们的技艺情况不得而知。而且,像吴桥杂技传统的魔术、杂耍等日趋消亡,从艺者也不好掌握。在推荐认定吴桥杂技代表性传承人王保合时,曾有同行提出异议。但经过工作人员逐村走访、了解传统魔术的从业老艺人,并多方联系打听在外演出的杂技艺人目前的情况,在掌握综合情况后,确定了王保合作为推荐人选,使得同行心悦诚服,一致赞成。
景泰蓝工艺大师张同禄就曾表示:“国家在寻访认定传承人时,关键看艺人、工匠的技艺水平和传承情况。而我能有幸成为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之一,都是得益于这些认定标准。”
据张同禄介绍,景泰蓝技艺是外传珐琅技艺和本土金属珐琅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明清两代,御用监和造办处均在北京设有专为皇家服务的珐琅作坊,技艺从成熟走向辉煌。而北京景泰蓝技艺复杂,工序繁多,综合了青铜工艺和珐琅工艺,继承了传统绘画和金属錾刻工艺。他自己学的就是这门传统技艺,熟知并掌握景泰蓝的创作设计、全部生产的工艺和管理。
张同禄感慨地说,保护景泰蓝,最重要的是要从保护知识产权入手。大师们钻研设计出的造型,常常被一些小工厂剽窃,使用粗劣的原料加工,在街头兜售。市场上虽然也常常能见到这些类似景泰蓝技艺的制品,可很少运用到正宗的景泰蓝制作工艺。即便这些作品有的造型典雅、色彩绚丽,但缺乏“传承有序”的特点,始终也不可能归入“非遗”项目的传承体系。
一种“非遗”要认不同流派
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一个项目的申报地区涉及到了中央、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辽宁省和山东省,并且相关的传承人多达20多位,成为了“非遗”认定工作中的一个典型的大工程。而给相关认定工作提出如此大挑战的主角就是我们的国粹——京剧。
京剧有“京派”和“海派”之分。京派以北京为中心,亦称“京朝派”;后者以上海为中心,包括南方地区的京剧,亦称“南派”或“外江派”。众多的流派把京剧表演艺术发展得淋漓尽致,丰富了京剧表演艺术的欣赏层面,京剧艺术本身也在流派的形成和繁荣中走向中兴。然而在“非遗”的认定时,既要考虑到各个流派的特色,又要兼顾到不同京剧行当的特点。因此梳理、认定如此繁复的项目不光要考虑传承人的问题,还需要权衡不同艺术流派所产生的附加问题。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负责人透露:“首先我们要确定该种项目存在哪几种艺术流派,避免艺术上的分歧。而且我们会更多地考虑这个流派被学术界、行内和当地群众接受认可的程度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独有风格特色。在此基础上,再认定不同流派的代表性传承人就容易得多,也清楚得多。”通过这种规范的操作,最终一份包含李世济、张春华、刘秀荣、刘长瑜、李金泉、杜近芳、杨秋玲、谭元寿、梅葆玖、孙毓敏、赵燕侠、李维康、叶少兰、王金璐、李长春、张幼麟、李荣威、周仲博、汪庆元、尚长荣、陈少云、王梦云、孙正阳、关栋天的24人大名单出现在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非遗”出现“重申报 轻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晓明认为,随着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定工作的开展,各地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积极性很高,但应防止出现“重申报、轻保护”现象。一方面,部分贫困地区列入名录的保护项目,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尤其是不少贫困县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经费而无法实施保护措施;另一方面,一些传承人抱着“先申报再说”的心理,申报成功后,在无法获得经济回报的情况下,也就对传承保护不再热衷。目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何评估、如何保护,各地还缺少全盘考虑的整体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涉及到传承人挑选和培养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20年至30年的远景规划,才能对艺术形式的整体传承形成保护。随着各级保护名录的制定,保护措施的延伸,保护项目将逐渐增多,贫困地区保护经费的压力将更大。贫困地区财力有限,尽管申报积极,但如果后续经费跟不上,最终只能无奈地出现“重申报、轻保护”的尴尬局面。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制定远景规划和长效投入机制。
今年已经完成普查备案制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说,为了规范我国对“非遗”的保护,政府有关部门努力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工作,今年是普查的收尾年,要编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省分布地图集》,打开这个图集就可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各省的分布情况。
文化部今年还要公布第二批“非遗”名录,同时要加大对列入名录项目的管理,对于怠于保护或保护国家级名录不力的地区,建立“黄牌警告”制度。对于传承人的管理是分级管理,国家级传承人由国家出台政策管理,省级由省级管理,以下类推。而且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立法进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制保障。
由国家最高文化行政部门认定和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艺人的热情非常高。但由于受名额的限制,个别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推荐及评选,确实也产生了一些争议。如今年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申报工作历时近一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直单位共推荐申报项目2540个,最后进入新入选项目的仅为510个。很早就有学者指出,传承人限制名额评选,多少会对没有被认定为传承人的艺人造成打击。而改变这种局面的方法就是改申报制为普查备案制。
而且,宣武文化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走访、整理和申报过程中,老艺人们不会用电脑,对于申请程序也不甚理解,因此,用电脑整理照片、资料,上传到网上宣传,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材料等工作都是他们一手操办的。
北京京城百工坊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放也向记者表示:“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申报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文化的发展与延续。”他担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只能按照规定数量申报,根本无法与民间存留的文化样式的数量相匹配。这样一来,可能某种文化“熬到”能申报的时候,其本身已经消失了。文化部去年6月公布的第一批22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就有已经去世的两位传承人,分别是川剧的传承人陈安业和苏剧的传承人蒋玉芳。
京剧走进课堂模式可以推广
近年来,我国日益强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吴祚来认为,文化遗产日不仅是展示全国文化遗产的日子,也是研究与思考我们如何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时刻。许多文化现象都出现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文化生态之中,它们也有着一定的文化生命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心态与艺术表现方式就会发生改变,艺术样式与节庆仪式等等,也就随之消亡或变异。所以,如今更多传统的、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通过博物馆中展示的方式,让人们看到它存在过、影响过一个地方或一个时期的人们。而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一些节庆形式在他们那里更是有了新的内涵与表现方式,这就是文化变异,它继承了一些内涵,却又加进了自己民族所需要的内容,几经传承演变,就迥异于中国的相应文化源头了。
目前,像京剧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开始进入课堂,这无疑是一项意义积极而工作巨大的文化工程。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坦言,让京剧进校园确实也有一个各地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比如说在一些地方就可以让地方戏进校园,如广东的学生可以选学粤剧,四川的学生可以学唱川剧,陕北可以让陕北民歌进课堂,让安塞腰鼓进体育课。”
国家5年超两亿救济“非遗”
“我们的‘葡萄’每串价格定在1200元,大多数人都愿意去买便宜的,几乎没有收藏者愿意接受这昂贵的价格,几年来,我的‘葡萄’只销售出两三串。靠这门技艺是无法维持生计的,自然没人愿意学了。”“葡萄常”传人常弘表示,“‘葡萄常’一旦成为了商品,就意味着贬值。”虽然她不愿看到有100多年历史的祖传的技艺贬值,但找不到徒弟,市场化的路又行不通,现在她也只能在等待中寻找机遇。
资金短缺、后继无人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公认的难题,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葡萄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传承人常弘告诉记者,北京“葡萄常”从出现至今,经历了几起几落,从清末慈禧褒奖,到上世纪40年代衰落,上世纪50年代复生至60年代又一次衰落,1979年回生,第二年再次散伙,1982年回生又再次消失,现在传承人虽已将技艺再度恢复,但也只是象征性地做出几件作品,而且寻找徒弟也十分困难。北京市民间艺术家协会秘书长于治海说,他为“葡萄常”在当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立足担忧,也对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疑问重重。相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传承人,更多被列入“非遗”保护名单项目的传承人生活在欠发达地区,如传说、年画、民间绣活、锣鼓艺术、游艺与杂技等“非遗”传承人生活困窘的现象十分普遍,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就更加困难。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赵书认为,政府可以采购传承人的作品,或通过博物馆购买、收藏、展示当代民间大师的工艺精品等方式,给予传承人一些经济补助。首都博物馆姚副馆长介绍说,首博已开始在每周六的固定时间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活动,并代表首博邀请传承人前来参与这种活态的展示,同时愿意为传承人解决资料整理、道具保存等难题。同时,首博还将给予传承人一定数额的报酬。
日本“非遗”项目并非终身制
同时有专家认为,要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必须进行产业化开发,只有被市场所认可和接受了,才可以反哺对其挖掘和保护,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民俗专家王作揖表示,由政府投资恢复和保护是一个前提,但最重要的还是申报成功或恢复之后如何长久延续发展下去,如果产品没有市场,年年靠政府拨款养活,恐怕还是难以为继。保护也应对具体品种具体分析,有的品种如果市场有需求就应该全力支持,在保护中求生存、求发展。政府的资金支持不能是无偿的、无休止的,而是在保护扶持下让其自谋发展。
另外,我国政府对遗产传承人要扶持与监管并重,不仅要制定严格的传承人标准,还要对经费的使用承担指导、管理之责,并监督该项遗产传承的状态。一些传承人在得到经济帮助后心态发生变化,或是安于享乐,或是追求金钱,还有些为了确保自己的经济收入而拒绝传授技艺,反而危及到遗产的传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监管制度的缺位,使各类隐忧日渐增多。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权基永介绍,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均有较为成熟的做法。韩国在为遗产履修者(学习者)发放“生活补助金”的同时,要求他们必须跟从传承人学习6个月以上,并在相关领域工作1年以上。政府还定期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状态进行审查。比如,他们要求国家级的表演类遗产每年必须有两场以上的演出,此举一来是对国民进行遗产知识普及;二来则是为了对遗产传承现状进行质量检验,如果认定该项遗产已不符合国家级的要求,政府就会解除它的称号。
日本政府定期给“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拨款,其传承人关于该遗产保护和传承活动费用都由这笔资金支付;政府的经费更多情况是拨给遗产保护项目的民间团体,资金使用上就更加公允合理。此外,两国均有认定和解除传承人称号的制度。日本的“遗产”传承人在拥有经费使用权的同时,还需要在获得“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称号的3个月内公开该项“遗产”的技艺记录。当传承人出现住所变更、死亡或其他变化时,其子孙或弟子要在20天内向文化厅长官提交正式文书。传承人去世后,其称号也不能由其徒弟承袭。(北京商报 李江 吴颖 李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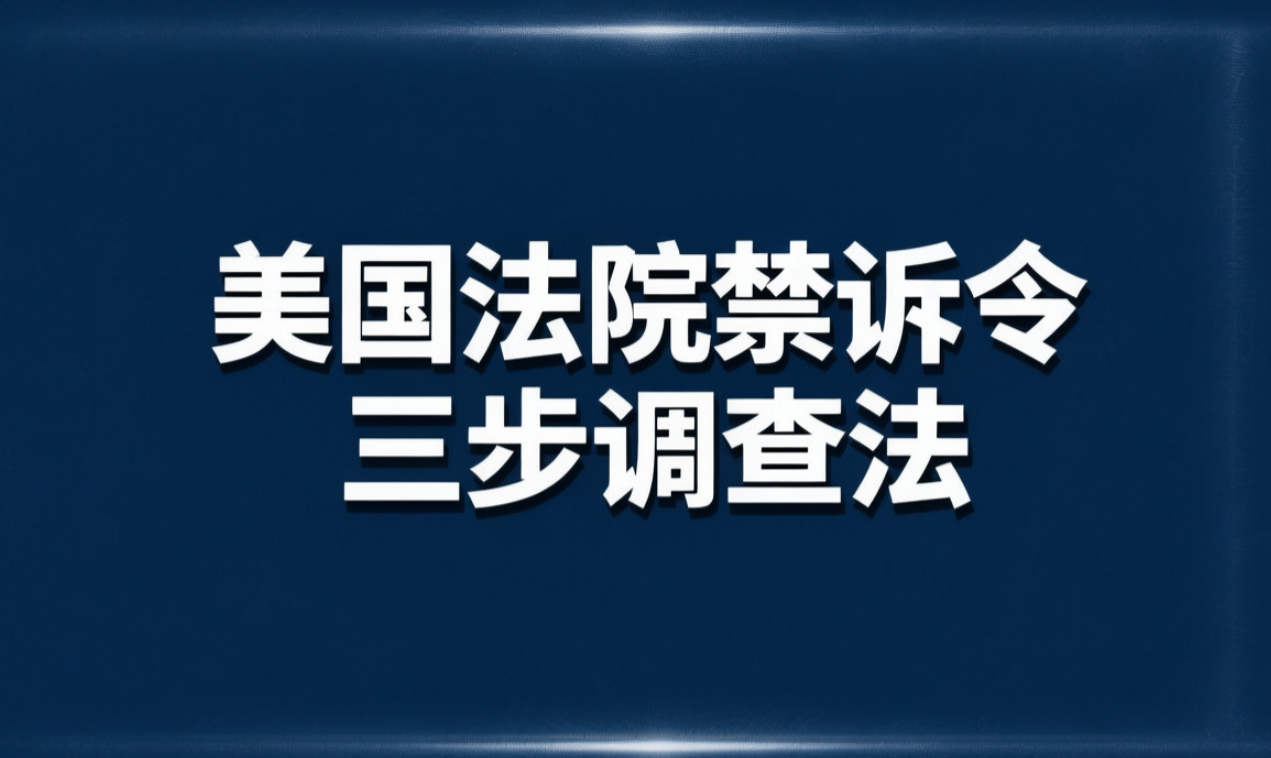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上一篇
上一篇 





评论